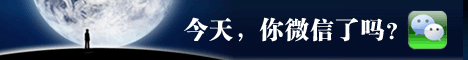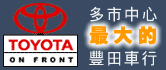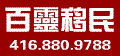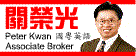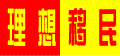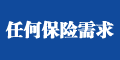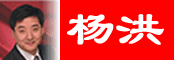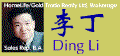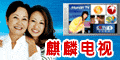中国艾滋遗孤生活实录
编辑发布:jack | 2003-08-26 18:31:55
【星网专讯】这是一份由164个孩子的名字组成的特殊名单。
尽管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开篇已成经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我们还是寻到了不幸家庭的相同之处――164个孩子家里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而相继离世。
孩子们都是孤儿,并且是以当地人“禁忌”的一种方式成为孤儿的。
编写名单的高耀洁已经很久不再跟别人提起这个名录,就在一年前,她还常把孩子们的情况挂在嘴边,她那时的愿望是每个孩子都能有个新家,有爸爸,有妈妈,有饭吃,有学上……尽管想领养孩子的家庭并非少得可怜,她的计划还是流产了。“这个事情太难做了,不光是领养手续复杂。”高耀洁很无奈。
于是,孩子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家乡,打理着成年人都感艰难的一切。
还有一份更庞大的名单高耀洁始终没能做出来,也不想继续做下去了――父母染艾滋病辞世留下的孤儿究竟有多少?是1万,10万还是更多,连高耀洁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
有6个孩子例外:
在山东曹县苏集镇的5个村庄里,6个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遗孤已经在新家里生活了半年多,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高萍15岁,最小的王淼只有6岁,其中两对姐弟被不同的家庭领养。6月16日,我们来到山东了解孩子们的真实生活。
刚过青丶,口音便有了明显变化,这里隶属山东菏泽地区,地理上却更近河南商丘。
实录一:
高萍的新妈妈葛玉勤因“人言可畏”感叹:做人很难很难。腼腆的高萍和弟弟半年没见面了,她与弟弟之间有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15岁的高萍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她想报考县里最好的一中,这让起先规划她“读师范,教小学”的高耀洁很有些意外,苏集镇的领导为此给高耀洁打了电话,“萍萍还是得考重点中学,她的成绩是全镇第一名。”
由青丶通往高新庄的路面在翻修,高萍的新妈妈葛玉勤就一直站在家门前的扬尘中等我们。
小院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清晨4点,葛玉勤要骑着它去5里之外的地里浇水。在这个农忙季节,丈夫王锁德远在胶州半岛的东营开车运货,使得葛玉勤不得不操持了全部家务。家里4亩多地种了棉花、芦笋、花生。芦笋正是收割的季节,但今年的收成和价格都不太好。葛玉勤说,去年亩产有2000斤,每斤的收购价格有2块多钱,而今年的亩产只有1400斤,收购价格才1块多。身旁帮他打理的兄弟说,最低时6毛多也卖过。
正屋墙上挂了不少高萍的的照片,八仙桌下全是空啤酒瓶,粗数数,有七八十个的样子,看得出,辈分高的王锁德很好客。“你王哥是场面上的人,庄里常有人来家里坐坐。”
因为领养萍萍,葛玉勤已经招来不少闲话,村里有人说,“养个孩子就是为了捞钱。”来自高萍河南老家的传言更令她气愤,“高萍被卖给人家做小媳妇,连学也不上了。”“做个人很难很难。”葛玉勤哭了。
闲话总是流传很快,使得“很在乎脸面”的王锁德烦了。他和妻子找来高萍,认真地说,“萍萍,你要想走,我们给你路费,你要留下来,我们也一定让你好好读书,你自己选择吧。”高萍留了下来,葛玉勤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我们不要任何人的钱,我们也不图这个,就是想让孩子好好读书,不再受这个罪,即使我们日子过得再艰难,也不让孩子遭这个罪。”让她宽心的是,尽管很多细节她都不和高萍说,女儿还是很懂事。
高萍是河南新蔡县小高庄人,父母于1993年开始卖血,1999年的春天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于2001年相继去世。没有父母的日子里,姐弟俩相依为命,却没能如愿得到亲友的帮助,当地政府曾经资助了一袋面粉和一堆煤,让孩子能够有饭吃住暖屋,但可怜的生存资料很快被自家的一个叔叔拉走了,连电灯和电表也摘了去,最艰难的3个月里,姐弟俩只喝面片汤,连盐都没有。
王锁德、葛玉勤夫妇在新蔡见到高萍时,第一个印象是“太可怜了”,很快作出把她带回来的决定。在农村,领养孩子有两难:一是女孩困难,二是年龄大的困难。葛玉勤说,这些事情我们都没考虑,就是想把孩子带回来,让她上学。
刚进晌午,葛玉勤读四年级的儿子王魁先冲进家门,打开电视搜寻自己喜欢的任贤齐。最近,他在生葛玉勤的气,“我妈太偏心,我要钱她总是不给,姐一要她立马就给。”但他和姐姐的感情还不错,“姐姐学习比我强。”
王魁带着我们来到了与正屋斜对过的东屋,这是高萍的房间,屋子布置清爽,只摆放了一床、一桌、一椅。靠近窗和床的墙壁上有铅笔写下的几句话,那是高萍的杰作,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高萍也需要用榜样激励自己。床边的墙上,最醒目的一句是“一定要争气,像(向)童第周学习。”而书桌前的墙上则是,“要想取得好成绩,就要多花时间作铺垫”和“人生能有几回搏”。
这一天高萍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5点起床去学校晨读,8点回家吃早饭,10点去学校上课,12点20分回家,3点再去上课,晚上回来的时间是6点。高萍就读学校的葛校长很关注这个特殊的学生,他说,“刚来的时候高萍的英语不好,也不愿意开口说话。”高萍不太同意校长的说法,“地理这样的副课成绩不太好,因为以前在河南家里没学过。”那时,高萍的最大障碍来自环境陌生。
高萍很腼腆,还没说话脸就会红。她说自己现在好多了,在新学校第一次被老师提问时,只回答了一半眼泪就流出来了。
弟弟高山被临近的水牛陈庄的一户人家领养,只有4里之遥,但姐弟俩已经有半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的情况是,高山不说姐姐好话,高萍也不叫家里人理弟弟,两个孩子中间有些莫名的芥蒂。高萍说,弟弟“太受钱的诱惑而被人指使”。――在高萍来到新家以前,曾经收到捐助款1700多元,她没有听从弟弟的意见交给“有恩于弟弟的人”,而给了葛玉勤。
就要读高中了,葛玉勤在为高萍的户口想办法,他说,高萍原先就读的学校校长彭晓辉已经帮助办理了相关手续,户口很快就能拿到。令她更骄傲的是,来时体重只有62斤的萍萍,已经接近100斤了。
这里的信息比较闭塞,高萍只知道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郑州大学。但这丝毫没能阻止花季少女的畅想,萍萍把自己更遥远的设计告诉了我,“要做记者。”理由也很实在,“我是经历过苦难的人,想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她的心目中,做记者最重要的是“尽职尽责,用自己的心善待别人”。
这天中午,梁堂村的支书张荣桂也赶来介绍情况,他希望记者能够把当地的特色和政策介绍给别人,希望能有人来这里投资。按照当地“女人不上桌”的老习惯,我们和支书张荣桂喝酒的时候,葛玉勤一直在灶房里没出来。
实录二:
13岁的乔小刚还是个孩子,很多和他有关的决定都不是他能做主的,诸如,管谁叫妈妈,诸如,为什么再换个新家。
尊敬的高奶奶:
我是乔小刚的大姐乔玉,谢谢您给我找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弟弟,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弟弟相处得很融洽。他刚来到我们家时学习不是很好,说实话,您收到的成绩单是假的,是我叔和老师商量好的。但在这几个月中,由于他的聪明和我的辅导,小刚成绩突飞猛进,很快跃进了班级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语文:87,数学:96)。有时日子是清苦点,但母亲视弟弟如同己出。
但是飞来横祸,母亲并非故意的一句话让叔叔听到了。尽管随后母亲就跟叔叔赔不是,但他不听,执意把弟弟拉走,还说要把小刚送走。我弟弟吓坏了,抱着树哭着喊着不走。但叔叔生拉硬拽,树被抓破了皮,弟弟被领走了。我和母亲找过他几回,想领回弟弟,但叔说:“我领回的我养,不用你们操心。”我母亲有哮喘病,常年吃药,这几天她打了十几天的吊针,人也瘦了十几斤。
……
现在弟弟见到妈妈就躲着走,母亲很伤心,为了躲避这一切,我在离家十几里的工厂打工,上的是夜班,正好治疗我的失眠。为了我的母亲,我已放弃我的学业,就让弟弟在叔叔家吧。
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乔玉2003年6月2日
村里的邻居详细地介绍了这场变局。
乔小刚是去年12月来到新家的。一天,妈妈把蒸馒头发酵用的“面起子”晒在屋顶后下地干活了,家里的钥匙就留在了小刚手里。没多久,小刚跑到村子里玩,下雨时妈妈急匆匆赶回来收东西,却找不到小刚,心急之下,说了一句“这个祸害”。不巧,被路过的叔叔听到了。
叔叔据此断定,妈妈在家里也不会待小刚好,便执意将小刚领回了自己的家。
此事在村子里也沸沸扬扬,他们都认同:妈妈对小刚很不错,叔叔这样做也出于好心。
赶到小刚的叔叔家时,婶婶正带着小刚和6岁的小妹妹在吃午饭――拌黄瓜、馒头,还有米汤。对于做过假成绩单,小刚有些惭愧,不过他说这一次的第一名绝不含水分。在庄上,小刚几乎没有朋友,在学校常在一起玩的也都是外村的。
对于不久前的变故,我和小刚没有谈及,希望他不要在心底藏下这桩事。和其他5位孩子不同,他自己一路寻到了高耀洁的老家――父母去世后,小刚一个人在家乡靠乞讨和拾荒养活自己,一个烧锅炉的看他太可怜,给他出了车费,从河南来到山东。
叔叔已经办好了二胎的准生证,但究竟是不是再要个孩子,叔叔还没有决定。
领养状况的尴尬――6:164:未知数
支书张荣柱去过河南新蔡县接孩子,为了接到另外两个孩子,他特地和派出所所长打了招呼。尽管如此,也有人说他的闲话,“把孩子卖了。”为此,他记了一个简单的账本,需要说明的时候就拿出来,“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侄子领养,一个在我表侄家,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在那呆了4天,花了1100元,还给了孩子亲属400元。这些钱都是领养的家庭出的,笔笔都很清楚。”
而13岁的高山在来到山东前,曾到过4个人家,叫过4次爸爸,他们分别在开封经营一家裁缝店,在宁陵卖豆腐脑,中牟县一位派出所副所长和省公安厅一位副处长。中间两位高耀洁都没有同意,怕孩子受气,另两位都在一段时间后把高山送了回来,原因很复杂。
高耀洁说,艾滋遗孤的回家路仍很漫长。
领养遭遇的更大问题是如何保证手续合法,至今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组织关心他们的未来,仅凭个人行事不仅难以解决普遍问题且手续繁琐。高耀洁仍很焦虑,她目光所及的孩子们的仇恨令其铭心刻骨,她曾自问,“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他们将走向何处?”由于孩子也沾染了“艾滋气息”,孤儿的现状总与歧视、贫困联系在一起。
孩子们读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第十册语文课本,有一篇题目为《一个村庄的故事》的课文:“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过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8月,……小村庄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锋利的斧头和靠斧头得到的一切,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遭遇的现实。
(本文中的艾滋病遗孤均使用化名)
(本文摘自《新民周刊》,作者:李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