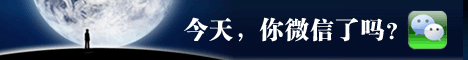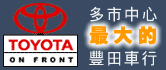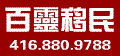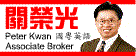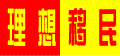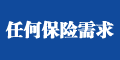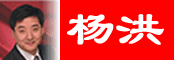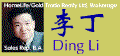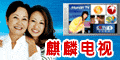亲历共军淮海集中营(1)
编辑发布:jack | 2006-01-04 19:05:12
【星网专讯】――国军第七兵团溃败前后见闻
作者:冰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俘虏敌人,或作了敌人的俘虏,这等事在一个军人来说,其普通与平常的程度,有过於战争的胜败。西方国家的军人们,在战斗中若认为自己已经尽责而濒力竭之际,被敌人所俘获,他们往往是称之为:“光荣的作了俘虏。”或直截了当的称之为:“光荣的投了降!”中国军人由於所受的精神灌输是:“宁死不屈”以及“不成功、便成仁”等教条,所以将曾被俘视为耻辱,只此一点,就可看出中西军人的“光荣”标准,是绝不相同的。
记述国共内战的报导很多,唯独对共军俘虏营内之风光,尚少见到,其原因或即与“光荣”标准有关。笔者以为;战败被俘,并不同於淫荡失节,大势之所趋,岂可将耻辱归於不幸的军人?现将其中向少人知的秘情,凭记忆所及,据实忆述於下,当为读者所乐闻。
**最严重的是吃饭问题
民国卅七年的十一月廿一日,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特别坏的日子,事实上;那天的天气,在那半个月中,还算是一个上好的天气!殊不料末日竟随着夜幕的撤除,静悄悄地到临这块废墟中的阵地之上了。这新到临的日子,便是本文所叙述的种种内容开始的一天,但也是一场凄厉的大战争之第一个环节落幕的一天!
太阳还未跳出地平线,大地一片苍茫,阵地中的战士们一个个皆从洞里、穴里、沟里以及窖里向地面探出了头,或爬出了地面,每个人仍如一往般的展开了当天的活动:点查人数、检验武器、添补弹药、擦抹炮膛、修补工事、埋葬尸体……
但有若干事项却临时免除了,那就是最重要的:开饭一项。因为开不开饭,是要由南京的政府方面决定,并且还要等空军的飞机送了来,谁若想到吃饭的问题,就要向天空多看几眼。当例行勤务作完了之后,就又都自由自在的或坐或卧下了,有人在出神,有人在发呆,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在惺忪着睡眼去斗牌。
二三十个显然一夜不会阖过眼的人们,在薄薄的晨雾中,走向了阵地的边沿。这群巡视阵地的人们,全部是将领,除了七兵团司令部的人员外,还有六十四军及一○○军的,另有许多周围地区的友军军官和联络官,还有几名是由周围阵地上撤退来的作战人员:有四十四军的、也有六十三军的,他们在这阵地中,大多皆已没有了部队,作客般的一股脑都挤在司令官的周围。
**三个俘虏竟系作说客
众人在阵地的西南角上走着,司令官向守卫问:“这面有动静吗?”“没有,八义集方向,连枪声都没有!――”这个答话的,是个低级军官,他还未说完,司令官就向他点了点头,之后,大家就转身向阵地中间走。
此时,北面村庄的炮声开始了,“是四十师和炮三营向外发射的!”有人说。“报告司令宫!小碾庄取下来了!”有人来报告。“嗯!”司令官没有表情的答,显然对这个“捷报”不感丝毫兴趣!
“还有三个俘虏!”报告的人继续说。“人呢?”参谋长插嘴问。“押回司令部了!”报告的军官答。“知道了!”参谋长说。那军官行了一个礼走开了,这一群人,就在阵地中继续巡视了一会,最后依然又都钻回司令部的地窖。
大家方在地下室里各自找了一个墙角落蹲下或坐下,士兵们竟将三个被捆绑着的“俘虏”,於此时送了进来。当众人向俘虏一看之余,不由人的怔了一下。
“这是怎么说?”二十五军军长疑惑的说:“这是什么俘虏?――解开他们!”士兵略一迟疑,见到众人未说话,就即刻为那三人解开了绳索。那三个人活动了一下手臂,舒展了一下腰部,就向司令官鞠了个躬,也向众人点了点头。
“他们是谁?”司令官知道众人认识这三个人。
“司令官记不起了,”二十五军军长,指着其中的一个说:
“他是四十四军办公厅主任――魏主任,月初在新安镇会报的时候,到过会。那一位――”说着,他又指一指另一个:“是八十三师的副师长――”他记不起姓名了。
“报告司令官,职在瓦窑被俘――”一个“俘虏”自己说:“职是六十三军副官处长。”
“好了――”司令官先绉了一绉眉头,接着就用右手的姆指和食指,夹着自己额上的两边太阳穴,上上下下的活动了一会说:“你们说说吧――随便怎样说都好!”
**难以扭转不利的局面
三个人略略的犹豫了一下,就先后相继约略的说了一些阵地被攻破以及被俘的经过,之后,就说出了正题――“共匪军送我们到小碾庄,目的就是让我们做个传话筒的,如果司令官准许,我们就毫不隐瞒的报告――”说着,就注视着司令官,等待回答。
“说下去!”司令官一丝苦笑之后,又说:“我已说过了,你们随意怎样说都可以!”说完,自己就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姿式。
“这次我们兵团被围,围在我们周围的共军,共计是七个纵队,而在大许家一线阻截二兵团及十三兵团的共军,却有十二个纵队,较围困我们的兵力更多了五个纵队,论形势不用我们多说,司令官及诸长官都会知道,事实上,这场仗再打下去,也难以扭转不利的局面,送我们回来的共军头目,当然嘱咐了我们许多话,目的是让我们转报司令官,希望不再继续流血,像枣庄的五九军、峄县的七七军以及雎宁的一○七军孙军长那样就地停战,其他的话,我们实在不便说,司令官当然也能想到我们是来作说客,是来劝降的,不过有些事,我们可以表达一点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六十三军、一○○军和四十四军的将佐们,都受着所谓宽大的优待,可以说是事实,其他的,似乎也不必再多报告了。”
三个人一口气说了十几分钟,还待说什么,司令官伸了一伸手,手心向着他们说:“好了!我想不用再说了,你们休息一下去吧!”司令官说完,想了一想又说:“照理,我当任由你们自作去处,然而现今是在作战,只得委屈你们一些了――喂,把他们交给特务一营,不过,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几个兵就将那三人带走,他们并未作任何表示,竟随士兵去了。至此,司令部里,虽然还是那么多人,但却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每个人差不多都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最敏感的是那些老兵
除了高级军官有着消息,能够明了局势之外,如果他们能保守消息,那么,照理各中下级军官以及士卒,可以说对於整个局面,应当是被蒙在鼓里的才对,然而,却其实不然。人类本身就是半路神仙,潜意识和第七感,都似乎对人们有所启示。别以为有些人在那里晒太阳和打盹,也不要以为有些人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打牌、赌钱,其实,局势到了什么地步,似乎人人心里都已有了数。
最敏感的应当是那些在军队中混过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兵,他们犹如农夫推测风雨一样,能够准确的断定火候,但是他们也多半是听天由命派,对什么都看得很淡,凡事都是顺其自然。
年轻的低级军官们,有绝大的数目准备着决以死战,大多数的士兵们,并不是欠缺思考能力,而实在是,对於战争的胜负,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所谓。因此,他们的精神皆寄托在纸牌上,否则,到泥土下面去挖虫卵、找田鼠、掘青蛙。
只有中级以上的军官们,不论蹲在阵地中或是伏在隐避部,以及挤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默默的思索着,尽管他们已对援军的到来失去了信心,但仍不时的希望着南京或徐州方面到来的消息,其焦急等待的情况,一如士兵们盼望飞机送来馒头、烧饼和肉包子相同。
**宣传品桃起厌战心理
也许那个时间,是恰恰在上午的九点钟正,突然,阵地的上空,连接的响起了数十声爆炸,银色雪花般的纸片,由密集而疏松的冉冉由天上飞舞着,飘落下来。“老八打过来了膏药弹!”(注政治宣传弹)。因为这种东西,在战场上已是见得多了。
在过往,部队上的政工人员,总是着令士兵们不准阅读共军的宣传品,但是,由於每次皆是极大数量的投射着,如何能够控制得了,所以事实上,士兵们对於这一类东西,都是不感新奇的。
“咦!这一次的不能唱!”当人们检拾到后,略略一看,就有人如此说。那是由於过往共军投射这等宣传品,常常是有歌谱能够歌唱的,而且对於那些歌曲,有许多国军的士兵们都能朗朗上口。
比如在抗战胜利后,国军初次北进的时候,共军大量射入国军阵地的一种宣传品,正面只印着“摸摸良心,朝天放枪”八个大字,背面却是印着一首音调易唱而轻松的小歌曲,是:“春风吹,暖洋洋,燕子双双飞南方,南方父母盼儿郎,鬼子已打走,为啥又打共产党;哎、哎、哎,为啥又打共产党?”当然,那是心理作战,宣传品的目的只是在挑起北进的国军之思乡情绪和厌战心理。
**限即日四时放下武器
然而,这时所射过来的宣传品,意义却完全不同过往的了,这次的,肯定的不仅是一种劝降的布告,严格而论,差不多似是一项命令,因为纸片的正面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令。”背面小字写着,“凡在解放战中的蒋军官兵――”大字是“投降者不杀、起义者有赏!”另有小字是:“解放军对一切蒋军俘虏的三大保证:不杀,不污辱人格,不没收私人的财物!”
就在这些传单,方由空中落至地面的时候,一份“最后通牒”式的正式信函,仍是由一名原为七兵团,而已被共军俘获去的高级人员,持着白旗,由共军阵地中直接送了过来。那是一封附有条件的劝降书,限令第七兵团的全部国军,必须於即日(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之前,全部放下武器,走出阵地。并指定如逾时未能遵令而擅敢顽抗,则全部歼灭云云。
似这样的一封信,尽管文字写得还相当礼貌,但是,如黄百韬等这些人,如何能够接受?那不仅是责任的问题,一些老军人的荣誉心,也促使着他们不能那么容易的“阵前起义”,当然,是时的各将领们自然也皆会清楚的理解到,其后果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但是,谁又能够决定什么呢?
**决定於下午六时突围
尽管他们也曾多次提出了一些计划,但是纵然是提出计划的人,其自己也难以相信能够发生什么效果,除了计议定是日下午六时决定突围外,甚至连突围的方向都不能决定。
六时突围的理由是:白日不能突围,因为目标太大。若是夜间突围,共军的警戒必定特别严密。在十一月,於苏北的大平原上,日落的时间是五点五十二分,若是六点钟走出阵地,几分钟内就是黑夜了,在那个时间,依照通常布防的习惯是,那个时间尚算白日,夜间的警戒岗哨,尚未派出,所以才选择这个时间。其实,这也只是一个不很可靠的理论而已,因为人人都知道,共军在外面的包围圈,必定是密密麻麻的。
至於不能决定突围的方向,原因在於根本不能考虑共军包围圈的层数,究竟哪一方面应当略微稀薄?依理论,背道而退,向阵地北面突围,应当合乎当时条件,但有人以为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应当直接向西,向徐州方向去。所以没有结论,只含糊的决定临时看情况,再行决定。
另外,也约略的做了些突围的方案,除此之外,大家也只有拖延时间了,虽然仍是先后接到了徐州总部的数通着令“稍安勿燥”的电报,但是谁还会真的以为能够出现奇迹?
**乾粮虽多可惜投不中
空军并未令阵地中的士兵失望,十余架次的运输机,投下了徐州一带百姓们做好的熟食――这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阵地之前前后后的三个废墟中,共计不过万余人,徐州的百姓,每户若是负责一斤乾粮,那么五十万人的徐州市,咄嗟之间就可办到数日之粮。问题只是空军由空中投下,由於飞机飞得太高,所以大部份投不到废墟之阵地中。落在阵地中的一小部份,就成了各单位争夺的对象,为了一麻包乾面饼,几个单位不惜以枪口相向。
时间是无情的,尚在各单位配领食物的时候,那一刻终於到来了,该日下午四时。方过了五分的时候,共军的一颗浓红色的讯号弹,就在碾庄的顶空里爆开了,刹那间,千发、万发、如冰雹般的炮弹,紧密的相继着,由四面八方射进了阵地。一时间,灰白色含有浓密硫磺气息的炮烟,笼罩了这三块小得似是弹丸的废墟。
起初的一两分钟,人们於仓猝之间还在各自摸索自己预先掘好的掩避壕坑,但许多人尚未钻了进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旅程竟提早的到临了。一切尚未死去的人们,卷曲着身体,蹲在由战沟的两旁向地下掏挖而成的洞里,摒息静气的向观世音菩萨祈祷,或者默默的计算着炮弹落下的数目,或者猜测炮弹的“弹着点”距离自己有着多少远近?
然而,那些炮弹却也一刻不停的落着,尤其那些运用延期性信管的破甲弹,以及弹头上夹放了烈性炸药的臼炮炮弹,它们不仅发出了凄厉的爆炸之声,同时也散播出了较空气更为沉重的刺激性气息;苦味酸以及硝基苯的窒息气味,不仅令嗅到的人们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更使人的喉咙由剧烈的刺痛而变为麻木。
**飞机助战也难挽颓势
渐渐的,人们的耳朵也不再灵敏了,但是地面一跳一跳的震动,人们还是能够清楚的感觉得到任何一颗炮弹之落地处距自己的远近,十尺、五尺,身体的附近,当然,也有许多人再也不能猜测了,因为炮弹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或身旁。
七兵团部的办事处和指挥所设在一个由铁轨覆盖的坚固的地窖上,似这样的地下室建筑,一般来说,炮弹是绝不会炸透的,是以在共军初次炮轰时,将领们在下面仍然不以为意。然而,不过十几分钟,地窖的上盖虽然未被炸开,但是地窖的周围,却出现倒塌现象。
倘若再继续震动,狭长的地窖,就会如同挤牙膏那么样的压了下来,这么一来,大家慌了。在别处虽然有危险,但危险程度或许不会大过这里,众人如此一想,就一个一个冲上了地面,从此之后,指挥、联络的系统,就彻底的瓦解了,谁也再找不到谁,竟四散而去了。
对於这种炮轰的战术,共军称之为“歼灭”,这个字眼实在贴切,因为一般所指的战斗,是“棋逢敌手”“拳来脚去”,但这一战却不同,这恰似将对方用绳子捆得紧紧之后,再吊了起来打,根本没有还手之余地。
就以碾庄来说,大大小小的炮最少也还有数百门,但是却无法向外有效的发射,因为共军围在周围无法估计的面积上,若散散漫漫无目的的射出去,是不能收到丝毫的作用的。但是;由外射入包围圈中的阵地,那是要多准就有多准的。共军这些炮的位置,自然有远有近,近的就在周围三、四里,远的可能会在三十里之外。所以被围的阵地纵然有飞机助战,也难起死回生。
**一排排作了光荣牺牲
如此密密麻麻的落着炮弹,虽然太阳还未落山,但阵地中的天色,恰似“日全蚀”一样,昏昏暗暗。等到炮声停止的时候,已是真真的入夜苍茫一片了。
炮声既停,没有死去的人们,是不能伏在地沟里不爬起来,因此,又复听到了那些勇敢的低级军官们嘶哑着喉咙大声喊着近乎凄凉的口令:“验枪!”“验炮!”“预备射击!”
沉重声音的快速武器――轻、重机关枪以及冲锋枪,在一时之间,如同黄河决堤似的向着阵地之外漫无目的的发射着,在此同时,有些不知由来的口令,在各个角落里喊着:“突围了!西北方向,冲出去!”,或者:“团长命令:东南方向突围,冲啊!”
本来还在准备重新编组的低级单位,在接到这些来源不明的突围令后,阵地中就略略有了骚动,部份人员,就一面射击,一面向阵地之外跳出,另部份人员仍在死守,而共军的攻击令,是时已由号角宣布了出来,喇叭声趁着随夜幕而降临的寒意,透过了渐渐散发的炮弹烟雾,传进了人们听不清楚的耳中,不禁毛发悚然。
然而,这是战争,在这等情况下,不论是敌是友,只要是血肉之躯,一旦遇上了枪弹就要伤亡,英勇的中国青年们,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就在这块荒烟衰草的废墟上,作着殊死之斗!守阵地的人,是在死守,攻击他的人,是在强攻。倒下去了!倒下去了!那些各为效忠於他们理想的健儿们,一个个用尸骨填满了那条划分阵地内与外的沟壕,一排排的作了光荣的牺牲。
**伟大民族的豪迈凤度
终於,阵地中的抵抗,越来越少了,机关枪的喉咙也疲乏了,手持着加了刺刀之步枪的防守者,静待着共军的攻入。
“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不杀!”――果然,不一会的时间,共军们踏着阵地外壕中,方才战死之同伴的尸体,进入了阵地,当第一眼看见阵中的国军人员时,首先就高声的喊出了这句话。他们在喊话的同时,手中所执着的枪的枪口,或指着天,或向着地,但却绝不向着人。这些士兵都是“服软不服硬的”,你既枪口指天,我又何必刺刀相向,伟大民族的豪迈风度,就在这生死关头上表现无遗。
守军们在对方这种近乎敬让的情况下,大多数一言不发的摔下了手中的枪:一个个首先局部停了战,共军们一组组、一队队向阵地中进入,国军们一夥夥、一堆堆的向阵地外面走出。这一场为期半个月的大战就结束了!只有在战争的意义上分出了胜负,但是;双方勇敢的健儿们之间,却看不出谁胜谁负。
走出阵地的人们,首先作个深呼吸,希望吐出胸中积郁聚的火药气息,接着,就是一面走一面挖掏耳朵中的泥土,人人的脸面,周身,都如烟熏火燎过一般。一旦死的威胁消除后,头脑的活动能力,也就顿时失去了过半。沉重的双脚走在荒原上,不择路,一颠一跛的在那些斩去了叶茎的黄豆根上踏着,一个个、一夥夥,在昏暗中,后面的跟在前面的背后,谁都没有思考过,到底要走向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