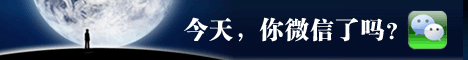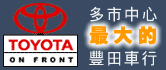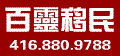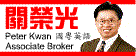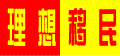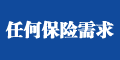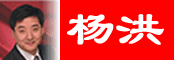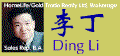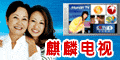亲历共军淮海集中营(3)
编辑发布:jack | 2006-01-17 17:49:55
【星网专讯】――国军第七兵团溃败前后见闻
作者:冰
(接上期)
**离开小村押赴旷野集合
十二月初,一天晚上,众人在河沟里洗完了脸,共军着令站队,大家不知是什么意思。共军却说不再回原处了,即时出发。幸而人们并无东西放在村中,说要走路,马上就走,谁也没得留恋,只是,又要去哪里呢?这又是一个新疑问。
这次只走了一个多小时,并没有进入任何村庄或城市,却是到了一个平原的旷野里,去到的时侯,已见到那里齐集了黑压压的人群,而且,之后,还从四面八方继续一队队的开来。
“这是干什么呢?”人们议论纷纷:“这里的人数恐怕有几十万吧!”
“那怎能知道,看样子是会有十几万的!”渐渐的,人们对此只感到似乎是成了无边无际的人海!
**愿留者纳愿去者资遣
大平原上,冷风卷着阵阵尘土,由於人多,又挤在一起,所以心理上,却不觉得太冷。大约到了夜间九点多钟左右,趁着天上的星光,颇为明亮,此时,“人海”里的几十处大扩音机响了起来,原来,在这纵横八、九平方里的“人海”之前,共军已搭盖了演讲台,不过既是夜间,又距离太远,在后面的人,自然无法看得清楚!只听着扩音机中的声音,是由一个浙江口音的中年人说的,话说得很慢,很清楚:
“蒋军的官兵们,我现在向你们首先宣布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命令,……”
他先说了对俘虏的政策之后,又解说了三大保证的范围,接着,就分析当时国共双方战争的局势,自然完全是在报告共军各处打的胜仗,最后就说到了当时的局面。当这个说完了之后,又换了一个人演讲,又是宣传了一项朱总司令对於俘虏的命令,他将这项命令,反反覆覆的解释着:
“愿留者――容纳。愿去者――资遣。”大意是说,有很大部份的国军官兵,其最初入伍的时间,是为了抗日之故,所以,任何人都不是罪犯,现在共军只是对付的一小部份“反动派份子”,不是国民党的人员……所以现在被俘的人员如愿参加解放军,是受欢迎的,大家共同联手解放祖国、解放全人类;如果不愿意继续作军人,而愿意回家生产,那么,同是为国家贡献,所以,由解放军支给盘川,遣送回乡……云云。
当演讲的人,都讲完了之后,又一个人来宣布“阵地首长”的命令,谁是“阵地首长”?不知道,但命令是:
“现在,在场的全部蒋军官兵听着,由现在之后五分钟开始,所有的蒋军军官,一律向标旗的东面去,而所有士兵,都向标旗的西面去,不准许犹疑,不准许反抗,等我再说出‘行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行动――预备――开――始――行――动――”
**官是官兵是兵各走各路
命令既已发出了,虽然说不上有人反抗,但是,却普遍的犹豫起来了,人人都在暗想:不知共军是什么意思,而要把官与兵分开?究竟自认是兵好呢还是自认是官好?――其实,这问题自初初被俘的时候,人人都早已想过了,人人也知道必有如此的一天,却未料这一天此时竟到临了。
“瞒不住,只好说一半实话――承认自己是个很小很小,芝h、绿豆般的官就算了!”
由於人们都在犹疑,尽管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有绝大多数还未看见标旗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共军派出了一大队人,各个皆持着一只旗子,在当宣布分别官兵的命令时,临时列队在“人海”中间穿过,他们列成了一条直线,好似电线杆一般,每隔十几步之遥就站着一人。
扩音机中不断的催促,乱哄哄的一个多小时,官与兵才算分开了,果然,在军官那边所站下的人们,都是穿着军官服饰的,――马裤、吊袋、肩章带、铜钮扣、大帽徽。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仍是走来走去,各自都想看看有无熟人。由於人数少了,所以熟人反而多了起来,走来走去了一阵,竟见到了许多熟人!
“妈的!坏了,这次可真糟了!自己本想只说是个司务长,现在认识自己的人很多,这个可怎么好?”有些人竟又开始焦急了起来。
军官们由低级至高级,占全人数的三十分之一,共计大约有四、五千人。
此时,列队开到了一大队共军,他们竟每十几人分作一组,每组共军,由俘虏群中,圈出二百人为一队,仅半小时的功夫,就将四五千军官“化整为零”,编成了二十几队,当每二百人已经圈出了之后,立即开走。
当然,在此同一时间,士兵们自然也在编队,但是怎样编法?由於笔者未能目击,不便妄言;但凭猜忖,该等士兵,多数是被立即补入了共军行列。并且开去了永城、蒙城、宿县等战场,掉转枪口,立功去了。
**凌晨吃早饭十人一盆菜
军官们组成的队,由共军领着,一队跟着一队,直向西北方向开去,由深夜十时半出发,大约在凌晨四时许,就在一个不知名的村中住了下来;这一天,与既往的十多天,却大大不同了。首先:去到了那村中的时候,已经有了饭和菜准备好了,略略休息了一阵,就开始吃饭,――黄米饭(谷米)配着大豆芽烧猪肉,每十人分配一盆菜,菜盆放在地上,热腾的米饭放在木桶中,而且有洗得乾乾净净的磁碗和筷子,大家站着或蹲着,围拢在一起吃。
“民以食为天”;大家一见这等“排场”,不由得个个喜笑颜开,有许多自以为身份高一点的军官,一路上矜持着不大愿和低级军官谈话,此时,也照样的有了笑容。开始举箸的时候,有些人似乎想抢,但是十个人如何能吃得下如同洗面盆那么大的一盆菜?最后,像人耳那么大片的猪肉,还剩下了不少。
这一餐吃了下去,对着共军干部,立即就有了好感,而且也觉得他们似乎顺眼了不少。
当刚吃完饭的时候,共军一个个如同“待客”似的,由庭院外面走了进来,一脸和颜悦色的姿态向大家说:
“吃饱了吗?――路途中没法预备。”他客气的说:“现在大家要休息了,晚上我们还要出发。没有事,希望尽可能的不要出庭院,一定要防止暴露目标,我们的目的地是徐州,到了那里,生活会正常的!”他说着点点头走了出去。
民房的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麦杆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更特别的,乃是每间房的门,不再关着,而且没有卫兵了!
“妈的!老八收买人心!”有人嘴里如此说着,一头向麦杆草中倒了下去:又松、又软。脱下身上的棉军服,盖着,相当暖和;有大衣的,那就更加舒服。
**听说到徐州大家都纳闷
睡不熟,或者有心事的人,可以自动由这间房,到那间房去“串门子”,没人过问,最低限度,在这个庭院中有了自由。显然,共军“葫J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大家还根本一点摸不清楚。一句话:“没有信心!”所以个个皆怀着鬼胎,静静观望。
中午,共军又挑担着水桶,送来了茶。四点钟不到,又开了饭,雪白的面粉馒头,菜是猪肉、白菜、豆腐粉条一锅煮,吃得人人一头大汗。
“诸位:饭吃过后,我们就要出发了,目的地是潘塘,今晚的行军沿途是公路,好走,不过倘若有飞机,希望诸位不要个别行动,相信诸位都懂,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共干说话斩钉截铁,但是,态度很恳切:“大家现在或者喝水、或者到厕所,请早准备。”
不一会,就出发了,一走出村庄,几千人又碰面了,仍旧是两百人一单位,后队跟着前队在公路上走,一路上都看得见的共军和民兵、运输队、担架队,来来去去,真是车水马龙,有些显然是急行军,走起来那种姿式简直如同运动会上的“竞走”,快得好似跑一般。
“看吧,不当俘虏,真不能想像共军的情况!”
“奇怪,他们没有丝毫辎重!周身之上除武器外,绝无他物!难道睡觉不盖被子?”
“用到你操心吗?――当他们须要的时侯,说不定洗脚水都有人预备好了!”
**老百姓的嘴脸十分难看
这群俘虏军官队,沿公路慢慢走着,途中所遇见的一切共军,虽然也有人投以注视,但从没有人作出鄙视的态度,只有老百姓的运输队,走在一起时,常常说着一些不大令人喜欢的话。
六点钟后,路上黑了起来,彼此看不大清楚,俘虏们反而心情轻松了一点;不知为什么,人人都不大喜欢看见那些讨厌的老百姓咀脸。实在奇,半个月之前,这里的老百姓都很友善,仅隔半个月的时候,他们竟变得那么可恨。
大家本来以为又要走一夜,但是仅走了三个多小时,潘塘竟到了。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村庄,村外有很大的一圈树林,虽然树密,但却都是落叶树,差不多全部树林,已经光秃秃的;然而,这树林边上,竟停着数百辆各式各样的车子,大坦克上还写着洋文字样。俘虏们就在这些车旁坐了下来,等待共军进入村中联络。
这地方是由苏北到徐州的公路,最后的一站了,过去,凡是奉调经过徐州的部队,由於不能在城市中扎营,多半都是停在这里,之后才越过徐州他去,故而很多人对这地方不陌生;不过,此次到达,心头上的滋味却与过往大异了!
**一位女共干宣布要学习
俘虏队在村前及公路上,略略停了几分钟,入村联络的共军们就回来了,之后,就一队一队的分批开进村中,由於这裹原有军营,所以这次没有再住进民宅,全部是住了军营。
当大家集中到过去战车团的操场上的时侯,起初以为不很大,但共军着令横排每排四十人,纵行,每行一百二十人,就如此,将近五千人,一刻间就站好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共军,穿军服,腰佩手枪,登上了操场的讲台,开始讲话,她说:
“诸位:由於这个场子太小,本来要让大家坐下来谈谈的,可是坐不下,只好略略向诸位谈几句,委屈诸位站一会――我们,奉上级的命令,为了诸位已经解放,在不久的未来,就要各自回到自己的故乡,参加祖国的生产建设,为了适应未来,上级着令诸位参加一段时期的学习。”
“现在,我们将要在这个地方停留一段日子,现在,有几件事,诸位要好好的与负责的同志们合作,倘若有任何疑问,任何困难,都可以向负责同志说明,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向上级反映。现在,为了学习工作进行的顺利和方便,首先须要编队,编队之后,今晚就暂时休息、睡觉,由明日开始学习。”
在这个女干部讲完之后,就开始一班、一小队、中队、大队的编了起来,共计编成了一个总队,辖三个大队,全数是四千六百八十余人。除了总队长、大队长以及中队长是共军干部之外,其他的小队长、小队副、伙食委员、内务委员、书记以及班长、组长等,都是由俘虏中,随便指出一些人担任的。
当一切编好了的时候,各小队长就被召去了总队部,其他全部人员,就分别列队进入营房。忙了大半夜,差不多又是到了近乎天亮的时候,才能开始睡觉。此时房内墙壁上,还贴着不少过去的标语、中山像以及军人读训、党员守则等等,在煤油灯下,大家睡在土坑上,眼巴巴的看着。
**填写“学习人员情况表”
大约睡了五个多小时,营房外就大吹哨子,各“小队长”们就催着众人起身,并且每人发给了一张纸:“学习人员情况表”。其内容一如通常的履历表,计有:姓名、年龄、籍贯、“在蒋军中服务科别”、“在蒋军中职务分类”、“部队番号、单位”、“官职名称”、“军阶”、“曾入何种党,社、团”、“家庭成份”、“有何专长”、“志愿参加何种工作”……等等,并且对於各项皆附有说明。
小队长一面向众人分发,一面着各人立即填写,要在吃饭的时候交回中队长。大家接到手后,虽然有点慌张,但是不能不填。有些人向别人东问西问,也有些人胸有成竹;不论是战战兢兢,也不论是马马虎虎,总算到时都填妥交给了小队长。
这营房很长,每排房中皆有十七个门,房的中间是路,两边皆是坑床。每排营房中大约住着五百七十余人,共计分住八排营房。当准备开饭的时侯,每个门口里皆有三几名共军等待着,俘虏们一个一个由房门外出,每出去一个,共军就着令其缴出私人财物,不论是钞票(金元券)、银元、金锭、金条、戒指、手表,除洗面用具外,不论任何物件,皆必须缴出。
交出之后,当即发给收据,并说明这些物品,在回乡之际当即发回,而共军并当即将该等物品写上人名,一包一包扎好,放入一个竹箩筐中,这一项工作,大约作了两个小时,就全部出到庭院,在各营房的门前,一班一班的开饭。
**缴交私人财物大闹笑话
关於缴交私人财物这件事,由於事先没有通知,因此人人皆未准备,突然着令缴出,临时无法躲闪,个个只好乖乖的拿了出来。不过,照当时的情况来看,能够拿出黄金钞票等值钱物的,绝大多数不是高级军官;许多阶级高的人员,很可能除了一个手表之外,别无长物。
然而,为了缴交私物,也曾发生了一些相当可耻的事,令共军登记的时候,不知如何下笔,诸如:裸体女人照片、春宫图及若干淫亵用品和药物。记得,当一个人缴屈了一些银色的小纸盒后,由於装璜很精美,共军小心的打开盒子来看,只见是些薄胶的小袋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也不知应当怎样登记才好,就问那物主:
“这是什么?”
“嘿嘿!嘻嘻!”物主只笑不答。
“说呀,这到底是什么?”共军有点厌烦。
“嘻嘻!”物主仍在笑,结果那共军真的由厌烦而变成了恼怒:
“你嘿嘿什么?有什么可笑?你是不是‘要洋盘’?”
“嘻嘻,气球!小孩子玩的气球。”那物主见共军生了气,就只好说话了。那共军面无表情的向另一个共军说:
“气球,十一小盒,共计:十的十二,加十二,合计一百三十二,给他收条。”
“妈的皮!什么玩艺,呸!丢脸!”站在门内等待外出的几个人们,在后面。
“这家伙是干啥子的?”有人在问。
“妈的,说起来活现眼,他是黄伯韬的副参谋长、姓陶的,叫陶文焕!”一个一面说一面吐口水。
“哼,”另一个也吐了一口唾i说:“有这等副参谋长,黄伯韬有什么办法不倒他妈的八辈子霉!”
“黄伯韬怎会用这种人?”
“那,有什么法子,他老子是国防部高参,一半人情,一半压力!――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似这等事,不知有多少宗。其间又有一人,在缴出私人物品时,竟缴出了二十支雷管及三磅TNT炸药。他一面缴给共军,一面向共军说:
“释放我时,一定要还给我哟!”
“你要这个干什么!”共军疑惑的问。
“我本来是作生意的,出来当差,误了发财的时间,你们放了我之后,到上海、到南京,去打劫银行、炸保险库,没有这些玩艺怎么行?”他认真的说。
“那还得请示过上级,这个好象不能算私人财物!”共军也认真的说。
“无聊!”许多俘虏看不过眼的说:“别罗嗦好吗!倒了霉,也用不到再滥下去!”
**学习讨论结论敷衍了事
当全营房中的人都出了操场的时候,就在各房门之前,一班一堆的吃了饭;接着,共军运来了大量毛巾、牙刷、搪瓷杯等,每人发给了一份,之后,就都回进营房。方休息了一会,共军又送来了大捆“大众日报”以及许多小册子。不过,看来这不像是有计划的“学习”科目,只是随便拿些书籍来而已。中队长说明要大家先看报纸,看完了之后,要分班研究、讨论,要作出结论来。
当然,这种“学习”,大家一来不习惯,二来也不知讨论些什么和结论些什么,那实实在在是敷衍了事。论敷衍,这些人们可以说个个都精熟,所以,到了下午饭后,共干就来听取众人学习的总结了。
当时报纸上的要点,多半是徐州一带战役大捷的消息,以及各地“人民支前”的热烈情况。似这等题目,有什么讨论的?因此,交出的总结,自然是些虚与委蛇的东西,诸如:“共军打胜仗,是由於吃得好、身体壮”或者“人多”等原因。当然,那些共干们显然并不满意这些,然而,接连的“纠正”过很多次,但是就没有纠正好,还是讨论不出什么特别的成绩来。
共干当然也明白,这些人并不是小学生,对於不想做的事,是很难做得好的,所以并不甚勉强,其真正的目的,大约也只不过要这些人们,能够了解一些当时的局势,――东北的“解放”、“南京的和谈”以及杜聿明、黄维等在徐蚌沿线“陷於泥泞”的情况;和傅作义、陈长捷在平津一带的被围等。换言之,也就是要这些人们相信国军的根基已真正的动摇不稳了而已。
**有人受不了宁死不唱歌
第一次上“唱歌”堂,就出了一项严重不愉快的事情,那是由於唱歌的题材,俘虏们不接受。事情的过程是如此:大约是一月五日的晚上,四五千人都集中在大操场上,由共干领导着学习唱歌,当共干先念过了歌词之后,就一句一句的,像教小学生一样的教法,自己先唱一句,接着要全体俘虏跟着唱一句。
谁知,教着教着,俘虏们竟全部不唱了,共干催着众人唱,大家皆不理也不答。正於此际,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喊着说:
“士可杀,不可辱,要枪毙由着你们,我是宁死决不唱的!”
随着这个人的喊声之后,略略一停,竟有许多人喊了起来“不唱!绝对不唱!”
那个首先抗议的是周昭星将军,湖南茶岭人,其当时大约仅只是个少中校而已。当时的哄动情况,是相当麻烦的,共干们也有着手忙脚乱的现象,经过了十几分钟,共干们窃窃商量了一阵,竟将歌词临时改动了,那是将一个“匪”字,改成了“军”字,重新又开始另唱,勉强算是上完了一堂。之后,共军不为已甚,终於在之后的日子中,从未再次唱这首歌。其歌词至今笔者已不能完整记得了,只还记得最前面的一段,那是:
“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解放大军功劳高来功劳高,千军万马如猛虎,蒋匪(后临时改为“军”字)兵败如山倒。蒋匪兵败如山倒,军长师长跑不了来跑不了,丢盔抛甲如脱兔,可惜终於进了网……。”
由於这次“事件”,也看出中国的军人,并不个个是贪生怕死的懦夫,铁血汉子还是多的。抛开政治立场不谈,在这件事上,也能看出共军们的忍让涵养,他们能够始终坚持上级的命令去执行国家的政策,依当时俘虏们的猜测,以为共军会处罚一些人,藉以镇压;至少,要制裁那个周昭星,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周昭星竟在第一批被释放的人员之列,那是后话了。
**大家明白人应说老实话
当时,既已停止了唱那首“打得好”歌,之后,就改换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海燕之歌”。
当学这首“海燕之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俘虏,江西人,名字叫潘宗韶(以后曾在台湾,任少将)竟向共军提出问题说:
“这是共产党的党歌,我们只是共产党的阶下囚,是些俘虏,让我们唱这歌,到底有点什么味呢!”
共军答覆说:“你们在现在并不是俘虏了,是参加学习的学员!”
潘某又说:“既不以我们为囚犯,那么,我说实话,至今我对共产党没有印象,所以,我也没有兴趣学这些,因为对我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我说我喜欢共产党,那是我骗你们,大家明白人,何必自欺欺人呢!”他的声调是很温和的。共军的负责人员终於说:
“如果不愿唱那也就只好不唱,解放军决不勉强人们做不愿作的事。”
以上,这也只是许多事项中的一点点而已,因为这项“学习”,由民国三十八年的一月初开始,差不多要到了该年的二月底才终结,前后应当是两个整月,中途又加进了许多新来的“学习人员”,那是由永城、蒙城以及宿县等地来的,其中除了第十二、十三、第二、十六等兵团的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番号单位。人数之多,只军官就有三万多,当然不能全部在潘塘这一个小地方容纳得了。因此,就迁到了徐州的九里山,一部份在九里山直待至这所俘虏营结束,而一部份,又从九里山迁向了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县一带去。这些变迁,自然是随着国共双方军事的转变而致。
共党对於这些俘虏的处理,是有原则性的,在起初只着令各军官俘虏,自行填写“学习人员情况表”,但是这种表,只要略略一看,就能发觉是一种完全无用的废纸,因为不仅绝大多数的职务、军阶等项都乱填着:司务长、司书、服务员、辎重单位的人力连排长等,而许多人竟填写了假姓假名,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其不真不实来。然而,共军明知其伪,但不指破,在许许多多次不嫌烦的个别谈话中,在许许多多的旁敲侧击中,早晚弄清了每个人的真正的姓名和身份。
**发现了草药大家装性病
在事过境迁之后,俘虏们於获释后、又络续回到了国军中,当彼此谈论在共军俘虏营中的往事时,曾经发见了几点当时看不出的事,其一:共军选拔了一切的具有特种专门技术的低级军官,用“教育”和“说服”的方式吸收了他们。那是:炮兵的测量人员、辎重兵及装甲兵的修理工程人员、通讯兵的报务收发人员、无线电的工程修理人员、以及低级甚至高级的医务人员。
而最先“资遣”的人员有两类:一类是广东及福建籍的低级军官。首先释放的原因,主要乃在於无法进行教育――共军中粤、闽籍的人员,无法调动那么多来从事教育俘虏工作;再者,也由於这些粤、闽籍的俘虏,与其他俘虏不易相处,所以,释放了事。
第二类是伤、病的人员――当时共军在徐蚌大会战中,伤者自然不少,其自身尚且无法立即增加医务人员,因此,当然更无法顾及敌军俘虏的伤病,况且,对於若干传染病,共军更l心其传播蔓延,如性病就是。所以伤病人员多是在学习了数日之后,即释放了。
为了俘虏们发觉了这些情况,可以提早被释,所以会有不少人冒充粤、闽籍人,更有许多人假装生病。关於冒充广东人,只要能说点简单广东话,也就行了。但是假装生病,却是不易,因为没有病徵,是难令共军相信的。为了希望被释放,不少人就冒险的制造病态。
说来有些可笑,如:在九里山时,每天由军营至附近的河沟中洗脸,某一个有点药草常识的人,竟找出了一种叫做茅莨的草,暗暗的采摘了一些,带回营房,夜晚在睡觉时,就用这种草,搓弄自己的生殖器,第二日:局部就肿了起来,此人大喜,就又告诉了几个熟人,如此一传二、二传三,不久,许多人竟都采用了这个方法,结果,不久之后,许多人也都“举步艰难”了。共军派了军医,只略略一看,就肯定的说:“梅毒!”
事实上,个个都肿得放光,自然军医才会那么肯定。共军负责人员却怀疑的问:
“为什么过去半月,未发见这现象,而竟於突然的两三天内,病了这么多?”
“同志!”这群“病人”解释着说:
“性病的治疗,需要很久,过去我们差不多每隔三、两天就耍打针吃药:消发代仙、盘尼西林等等,整天带在身上,所以表面看起来,不似生病,然而,至今被俘二十多天了,药力在身上消失光了,所以‘发疯又发了出面’,而且都是一起发!”这种道理说得太好,结果他们都被提前放走了。
**似乎有意让俘虏们逃跑
共军当时处理俘虏,有些事是令人多年来仍旧想不通的,那即是:有些俘虏因为地位高,不放回了,但有些军、师团长等级的人,共军把他们调到洪泽湖一带继续“学习”,久久不提释放的事,而又管理不严紧;大家见到那么松疏,有些人就鼓起了勇气悄悄逃走了――因为那里已隔京、沪线很近。
但是共军却似乎不会发觉减少了人员,也不追究,甚至连问都不问一声。众人见共军管理得既不严紧,逃走了又不追问,因此,就一个一个的逃跑,大概最胆小和最谨慎的人,最后也不是被共军释放的,而都是逃跑的,似这样情况的将领,如一○○军军长周志道、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徐蚌会战之前,国军中的风气有一项是:倘若某一人曾被俘过,虽然逃回来了,但既不能再担任队职官,而且要遭同僚的冷眼,甚至有许多同僚,不敢在人少的时候与之接近。但是徐蚌会战之后,国军的风气有了大转变,不仅许多被俘过的人,回来后,仍照旧作官,而於俘虏营结交的朋友在官场碰了面,除略略一阵“面蒙蒙”外,随即也就恢复泰然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