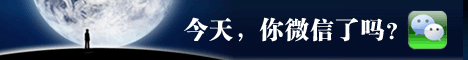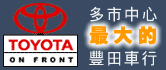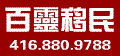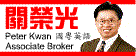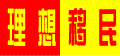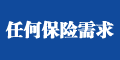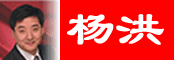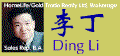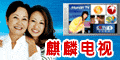回国散记:一位老知青的梦
编辑发布:jack | 2006-06-07 19:07:08
【星网专讯】(三十年后知青再聚;房子临街墙上仍保留当年写的两个大字。)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宏宇)1975年8月,我曾在山东省安丘县大官庄下乡插队。三十年了,我经常在梦中回到那个雾霭缭绕的村庄,大柳树下的知青小院……上个月回国探亲,这个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得知我海外归来,昔日一起在乡下泥土里滚过的知青朋友立即招呼在一起,在一家酒店里相聚。多年不见,大家的变化真大,当年的小伙子都已经人过中年,难以掩饰脸上的皱纹和渐起的腹部,是啊,孩子都快大学毕业了呢。朋友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腰缠万贯,也有的普普通通。可是不论贫贱富贵地位高低,唯一不变的就是知青的情谊,那是同甘苦,共患难中得来的,比金子都珍贵。
海阔天空交杯换盏之际,我流露出很想回到当年下乡的村子转转的意思。毕竟这么多年了,总是忙来忙去,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也不知道那里变成啥样了?这次回国,还不知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人生短暂啊。不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喜欢回顾过去的事情,珍视过去的朋友。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一呼百应。毕竟情况大不比从前,现在是要车有车,要钱有钱,只是没人提议罢了。讲好了,明天早晨八点钟上路。
实际上,当年下乡的地方距我的家乡不很远,也就是120里路。那时感觉很遥远是因为道路不好,中途要停停靠靠甚至要换车,回家一次要折腾一天呢。如今,山东公路系统建设的很好,县城与乡镇甚至许多村庄之间都铺设了标准很高的公路。一踩油门,个吧小时百十里路不在话下。
五个人分乘两部车,我和几位朋友坐在前面的尼桑车内,车主老高早已是省电视台驻本地的负责人,时任中级法院高官的老杜驾一辆进口美国焊马越野吉普车断后,沿途风光无限,朋友们指指点点。昔日沙土飞扬的土路和路边粉刷白粉的杨树,均已被宽敞平展的柏油路和路边宽阔的绿化带所代替。当日破旧不堪脏兮兮的路边店也寻不见踪迹,代之于气派的一座座饭店商号。只是路边的大片菜地庄稼以及道路上不时出现的拖拉机,提醒我们这里依然是农村。
很快就到了大汶河边上的一个集镇–高崖,这里距知青组所在地–大官庄八里路,当年我们经常来这里赶集。有时卖苹果,卖腊叉(一种自制的扬场工具),或为全组改善生活卖几斤猪肉。我还和同车的老张来这里卖过知青组自己种的菠菜,换回了两块多钱。现在想想很滑稽,就是为了这点钱,我们俩加上大队驻知青点的张大爷,推一车菠菜来回步行十几里路,耗去大半天的时间,这就是那时的真实生活。
高崖镇属于昌乐县,位于大汶河北岸,距山东中部的白浪河源头–高崖水库很近,河南岸就是安丘县的大官庄了。车过汶河大桥时,我们停下来,眺望着大河的上游和下游。现在是枯水季节,浅浅的河水在河床的中间静静地淌着,水面波光粼粼,我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曾经沧海难为水”吗?为什么这条河让我如此激动?
上车过了桥,没多远就到了大官庄地界。当年村西头这条坑洼洼的土路已经换成了一条平展的水泥路,路两旁是望不到尽头的塑料大棚。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里参加过秋收。晨露很重,钻进玉米地一会儿身上就湿透了,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露水。脸上,胳膊上被玉米叶划满血道道,痛痒难熬。
1975年冬天我探亲回来也是在这里下车,肩上还扛着从城里借来的一架手风琴。狂劲的北风吹得我象风车一样,我踏着积雪踉踉跄跄走回知青组,半边身体都冻木了。
我们知青组还参加了修大寨田冬季会战。寒风刺骨,雪花飘零,大镐敲到地上只是一个白点,我们手上都是血泡。挖引水渠时,站在冰水里挖泥,裤脚上结满了冰,走起路来噶吱噶吱地响。这平展展的土地上,洒下过我们辛勤的汗水。
来不及多想,已经到了村子中间。呀,村庄全变了,过去的草房都换成了瓦房,墙壁也不再是土坯垒成的了,当年的知青组在哪里呢?
我们一行人在村里转来绕去,寻找着旧时的痕迹。恰巧,我们遇到了当年的几位老乡,竟然还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知青组所在的位址,遗憾的是不见了当年那个热闹的知青小院,周围都是些新建的宅院。当年小院边上的那棵大柳树,如今孤零零立在那里,显的那么凄凉。
知青组小院南面的那条小河已经干枯,河堤上稀稀落落一些杂树。当年小河流水涓涓,岸边树木葱笼,我经常晚饭后提一个小凳,来到河边拉琴。月光从高处泻下来,树影婆娑,水波闪闪,琴声伴随我渡过了许多美妙的夜晚。
幸运的是我们在村中大道旁找到了昔日知青组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半排房子。这里原本住过十几位女生,面向小院,背靠大街。不过草房顶已被换成了红瓦,只是墙壁破损出显露出当年的土坯,说明还是旧物。更令人惊讶的是房子临街的墙上竟然保留着两个大大的红色黑体字,那是当年我写的一条大标语的一部分。
1977年春天,为了迎接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代表来安丘县乡下参观,公社组织了一批人在全公社和一些村庄的主要大道两旁制作了一系列大字标语。由于我美术字写的好,公社为我配备了几位助手,有的负责粉刷墙壁,有的帮我描字。公社一些主要路段的大字标语皆出自我手,眼前这两个大字就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杰作。
我凑近墙壁,仔细观察当年用红色粘土描成的这两个字,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它们还能保留下来?我发现这里曾经用白粉粉刷和覆盖过,但白粉脱落,红色大字再次显露。就这样,三十年来它们奇迹般地表现着,迎候着风霜雨雪和主人的回归,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经老乡指点,我们还找到了当年村中唯一的小卖部–“联社”的旧址,那房子还在,大门上着锁。同来的老杜乐不可支,跑到门前留了影。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售货员,还经常走家串户去社员家收购鸡蛋。记得那时候的鸡蛋三毛钱一斤(约十个)。那时候村里人的油盐酱醋针头线瑙纸张笔墨都去联社购买,老杜为人忠厚,做事耐心细致,最受村里男女老少爱戴。
当年我们风华正茂,满怀理想来到这里。尽管生活枯燥劳动艰苦,但知青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集体,大家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组先后出了七位大学生。在知青组旧址前,大家七嘴八舌,回顾着当时的许多趣事,心中涌起无限激情……
为了协助知青们的生活和劳动,大队曾派了一位老社员张大爷长驻知青组,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可惜这位老人十几年前过世了。我们见到了张大爷的儿媳妇-张嫂,当年她在大队缝纫组,给我铺过一次裤子,还给我当过一次“红娘”呢。
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叫“秀娥”,长的美丽大方,堪称村里一枝花,与张嫂同在一个缝纫组里做事。知青组里那么多潇洒英俊的男青年她不爱,却偏偏看上了弱不经风喜欢舞文弄墨拉手风琴的我,托张嫂前来说媒。那时我才19岁,对此事毫无精神准备,况且知青组纪律严明,不允许谈情说爱,于是婉言谢绝,让那位姑娘伤心了很久。两年后我考上了大学,离开村庄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张嫂说:“那位姑娘很有志气,一心要跳出这个穷地方。后来她远嫁东北,据说有了两个孩子,前几年还回来探过家呢。” 我跟张嫂说:“以后有机会见到秀娥,一定代我向她问好。感谢她当年的勇敢,我永远都会保留着那一份珍贵的记忆。祝她生活美满幸福。”
我们一行人沿着村中一条小路来到了大汶河边。这里当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河边的苹果园是我们知青劳动过的地方。春天给果树打药,夏天浇水,秋天采摘,冬天剪枝。我们挥洒着汗水,收获着甜蜜。这条上工收工的小路上,留下了我们无数赤脚丫走过的脚印。
如今森林已经不见,代之于连绵不断的养藕池和蔬菜大棚。老乡说:仅种藕一项,每户可以收入2000余元。加上种植西瓜和蔬菜的收入,一户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不在话下。从经济角度讲,大官庄的乡亲们是彻底脱贫致富了。
昔日印象中秀丽如画的大汶河如今静悄悄的,放眼望去黄沙滚滚,河床上甚至还有专事挖砂的大型机械和车辆。千疮百孔的砂坑和一道道深深的车辙,象是缠绕在大河身上的重重伤痕。我扭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
我们告别了大官庄,从车窗回望,那位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老乡,站在路边向我们挥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