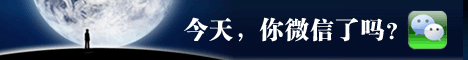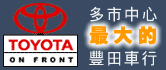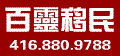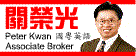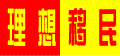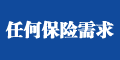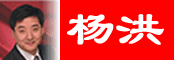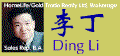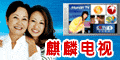旧上海的市井风情
编辑发布:jack | 2006-02-07 22:42:13
【星网专讯】在上海,没有什么能象那些比比皆是的弄堂使人能更了解这个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些邻里社区是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居家住所。他们不仅仅住在里弄社区,这儿也是他们工作、娱乐、社交以及日常购物之地。总之,弄堂就是这些居民的城市。相比之下,上海的那些高级的和广为人知的区域并不是普通人生活和活动的场所,甚至和人们毫无关系,里弄才是显示了大部分上海人生活真正的世界。
我们或许可以以弄堂的进口为界,把里弄生活在形体上(但不在文化方面)分成密切相关的两个部分。在弄堂口后面的房子里,是上海普通市民的隐私(有时候也并不那么隐私的)世界。弄堂外面的马路上,则是弄堂里日常生活的延伸。
**每天清晨的马桶展览会
上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与此不相称是大部分市民家中没有卫生设备。上海是最早有电、煤气、电话以及其他现代化便利的城市之一,但是直到这个城市发展的鼎盛期即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家庭厕所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仍只是一只木制的马桶,这一点基本上与偏僻的内地乡村没什么两样。倒马桶不仅是一项令人讨厌却又无法逃避的日常工作,而且成了都市生活清晨的序幕。
所有的马桶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是相似的:木制的,鼓形,大约十六英寸高,直径约一英尺,顶部坐圈为一英寸半宽的木边,一条铁质或黄铜的圆环固定住桶身,圆形的木盖上挖两只半圆形的凹槽以便捉取。马桶内内外外刷满了桐油以防渗漏及确保能长期使用,一般都漆成紫红色或金黄色。
由于马桶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往往作为妇女的陪嫁物。在这层意义上,马桶就好象诸如如今上海新娘的陪嫁物品彩电一样,但是更加不可或缺。马桶作为陪嫁物时,里面装了红蛋,象征并祝愿新婚夫妇能早日生育(尤其是男孩)。精美制作的马桶环绕着镀金环,桶身和桶盖上还描画着龙凤图案。这种马桶有时成了偷盗的目标。
如果附近有一所公共卫生间的话,男人们多半会去使用,这与乡下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事实上附近的公共卫生间也并不方便,因此小小的马桶就成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必用之物。一项很重要但令人讨厌的家务就是在上半夜将马桶放到后门外去,由收粪工负责将它们倒空。
收粪工通常在四五点钟到达,天还未亮,此时大部分人仍在梦乡。拖着黑色的有着两只红色车轮的粪车,收粪工进入里弄,喊着:“倒马桶!倒马桶的来了,倒马桶!”有时他摇着铜铃。声音划破了里弄的宁静,常常引起了一阵阵的鸡鸣。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作家用幽默的语调描述了这一场景:“大家小户,形形色色的马子。横七竖八,散兵线般陈列里巷中,如开‘马桶展览会’,猗欤盛哉!”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几乎有一百万户石库门房子的居民还在演绎着与民国时期差不多的收粪故事,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家庭厕所仍然是“亲爱的马桶”。
http://home.wangjianshuo.com/archives/2003/09/14/shanghai-france.club-old.whole.jpg
上海茂名路法国俱乐部。(资料图片)
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六十或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看见的是与其祖父母半个世纪前所见几乎相同的里弄场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上海的一个居民开玩笑似地用“壮观”两字描述那个时代的景象:上百只马桶摆龙阵似的曲曲折折地从弄底一直摆到弄口。住在沿街面房子的住户,甚至就将马桶放在昏暗的路灯下的街道旁。
粪车离开后,倒空的马桶置放在弄堂边上,接着就是早晨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令人生厌的事:刷马桶。主妇们所用的两英尺长由竹条制成的马桶刷很容易从里弄小店或摊贩手里买到。在弄堂里刷马桶,是女性家庭成员,一般是母亲或祖母的活儿。未出嫁的女儿基本不做这一事情。
一位居民回想起她唯一一次看见男人刷马桶的情景。那是春节期间的某一天,李锡康老人家唯一的女性,他的儿媳回嘉定乡下娘家探亲。不知为什么,当天晚上她没能赶回来。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一家人陷入了恐慌:谁来刷马桶?让年届中年的父亲或那三个十几岁的儿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刷马桶是无法想象的。较之于儿孙,老祖父似乎更合适一些,于是老人准备去做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这时,邻居彭太太伸出了援助之手。显然,她认为让一个大男人来刷马桶是不适当而且令人同情的。其实,只要每个月花上约一块钱就能雇一个女佣来刷马桶,但这种服务通常是以月为单位结算的。
刷马桶要使用一定的力气去清除粘在马桶壁上粪便。在清洗的过程中要频繁地加水、倒出。如放入一盆小蚌壳在马桶内,用竹刷子刷的时候就更加有效。居民们知道刷马桶的最佳时间是在粪便变干粘在马桶壁上之前。于是,当粪车一离开弄堂,家家户户便即刻开始刷洗马桶,场所通常是在居屋后门外靠近阴沟的露天空地。弄堂里于是充满了喧闹声,上海人幽默地称之为“弄堂奏鸣曲”。
主妇们辛勤刷洗马桶的场景在上海随处可见。直至1994年一位作家还如此形容:“每天清晨,八十万只马桶在弄堂涮响,成为上海晨曲的特殊音响”。马桶刷完后,居民们将之斜靠在墙脚让其自然晾干。通常不到半个小时居民们就都完成了这件早晨的工作。
**里弄小贩的吆喝声
上海市民有理由嘲讽清晨弄堂里的情景:全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以“东方巴黎”、“中国的纽约”、“世界第六大都市”着称。与成千上万贫民窟的居住者相比,里弄住宅区的居民还是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那只小小的木制马桶,同样的东西在农村已被使用了许多世纪了。
http://www.mrfujii.jp/images/history/02child/shanghai/postcard2.jpg
旧日南京路。(资料图片)
然而,粪车离开后的里弄生活景象才显出城市的繁荣,人民的小康和生活的便利。街头的商贩──他们贩卖食品,提供各种服务──以其特有的方式走街窜巷,劲头十足地做着生意──这些小商小贩描绘了上海日常生活的另一幅图画。
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
这是鲁迅1935年所写的散文《弄堂生意古今谈》开头所记录的上海里弄小贩的吆喝声。上海市民对此特别熟悉,因为小贩们每天走街窜巷沿街叫卖他们的货物。正如我们所知,鲁迅最后十年生活在上海,主要居住在里弄房子里。他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那所住宅,是虹口一幢普通的新式里弄房子,现在已是受到保护的遗迹。
http://en.chinabroadcast.cn/mmsource/images/2005/08/11/tra_osh_02.jpg
旧上海的街道(资料图片)
在许多场合,鲁迅以其着名的洞察力,运用杂文记录了上海里弄生活的情景。关于叫卖声,他写道:“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吃零食,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
小贩可以挤身于都市弄堂生活剧最活跃的演员之列。一大早,当粪车离开之后,他们开始贩卖大米、蔬菜等食品。于是,各类食品的叫卖声在都市里弄中回荡一整天,上海成了一处没有比之更便利的吃的世界。食品商贩是无处不在的,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人们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他们。
1935年,一位美国记者到达上海不久,发现“这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你还可以在上午随时享用午前点心:拌有火腿丁、虾米和鸡丁的汤面或炒面,或者是甜杏仁羹。下午的小吃有各式各样甜的或咸的豆沙馅、猪肉馅或菜馅的馒头”。这些食物总是在那些所谓的普罗(无产阶级)餐馆或者里弄中的大饼店里出售。但最大众化的和别出心裁的食品还得到街头挑着骆驼担的商贩那儿去买。
挑着骆驼担的食品商贩在上海到处可见;就如同作家哈丽德・塞甘特(Harriet Sergeant)所说,这些沿街叫卖的商贩 “将小吃变成一种上海风俗”。他们做买卖的路线并不是上海的大马路,而是背街后巷和里弄,那里才是绝大多数上海市民所居住的地方。
1949年解放后,老上海常常回忆起街头小贩所提供的各种不时之需的服务(诸如各类食品)和“过去那段美好的时光”。离开这座城市的上海人会怀念那些随时随地可以买到的形形色色的“小吃”,以及街头的各种吆喝声。
铁民(Tim Min Tieh,出生于1905年),一位在欧洲和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上海人,1940年当他准备离开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在里斯本等候去美国的轮船的时候,他想起了上海街头商贩的吆喝声。起先,他居住于罗塞尔市(Rossio)中心。“葡萄牙司机不断地按着车喇叭,其实街上很空阔,”
铁民写道,“每天傍晚坐在窗前,被迫听着令人发狂的噪音,回想起童年时代老上海街头摊贩们悦耳的叫卖声,对照是如此强烈,我不禁感到颇为遗憾。”于是铁民开始写了一篇题为《老上海的街头音乐》(“Street Music of Old Shanghai”)的散文,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写作不久就中断了。但他对上海街头如音乐一般的吆喝声的怀念并没有随之衰退。
四十年后,当他偶然找出那份未完成手稿,萌生了继续写了下去的念头,并最终完成了这篇文章。此文在他的一些对老上海生活鲜有所闻的年轻学生中传播。1993年夏天我访问铁民的时候,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而且双目失明,但仍在家中教授英语。他关于老上海生活的记忆依然极为清晰详明。
**各色食品随季节变化
上海弄堂里所卖的各色食品反映了季节变化的节奏。商贩将新鲜上市的节令食品很及时地带到里弄,以满足居民的需求。许多食品甚至在食品店里还买不到。例如,当新鲜的玉米刚刚收获,小贩将之放入铺着棉被而保温的漆篮中来到里弄中叫卖,“珍珠米,热腾腾的珍珠米!”这种玉米品质优良,鲜嫩多汁,香甜可口。
另一种大众节令食品是白糖梅子,晚春早夏当杨梅还是鲜绿的时候即可采摘。白糖梅子上市意味着江南被称为“黄梅天”的梅雨季节的到来。梅子包裹着白糖以缓解它的酸味,这种酸酸甜甜味道的使人十分愉快。仅仅提及白糖梅子就能引得老上海们满口生津。这种水果正好符合中国人评品好食品的三项标准:色、香、味。
白糖梅子因其颜色被人形容为如“白雪公主”,显示了西方流行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一位居民带着遗憾回想起这种水果,这一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上海人最喜爱的节令物品,到了六十年代逐渐匮乏了,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以粮为纲”。这导致江南大部分地区水果种植大量减少,而这里正是梅子生长的地方。
白糖梅子并不是解放之后,或是使许多农作物大量减产的大跃进之后,从里弄中消失的唯一食品。白果是另一种已经消失的食品。多少年来,夏日上海的街头有卖炒白果的。在午后,小贩们挑着一口圆底铁锅,以及一只简陋的炉子,出现在弄堂中。铁铲在锅中翻炒着,白果混合着碎瓷片,以确保能均匀地受热。白果和碎瓷片在锅子里发出嘎嘎作响的声音,这也是引起人们注意的手段。小贩一边炒着白果,一边唱着:
热白果来,热白果,/只只脆来,只只大。/若是要吃热白果,/─一块钱来买三颗。/─三块钱来买十颗。/─哎!又香又甜又是糯。
不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无不被炒白果的声音和悦耳的吆喝声所吸引。当小贩在路边或弄堂口停下担子,人们连忙准备好零钞,围上去购买新出炉热乎乎地包在纸袋中的炒白果。
街头的商贩是很有天赋的广告家。一些食物被介绍为具有轻微医疗效果或者很有营养的食品。例如芦根就被认为具有预防某些疾病尤其是夏天流行病的功效。这一功效由小贩的吆喝声而广为宣传:“哎!芦根当茶喝,明目效果强。夏天小儿用了它,包你皮肤不生疮。”
另一种食品梨膏糖,是自咸丰年间(1850-61)即流行于上海的特产。上海居民特别熟悉卖梨膏糖的吆喝声,小贩来到里弄,用苏北方言唱。吆喝往往用手风琴伴奏,总是一个曲调,可以更换不同的歌词,唱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吃了梨膏糖后的种种好处,以及不吃梨膏糖的种种坏处。
在冬天死一般寂静的夜晚,商贩依然做着生意,给他的顾客带来最喜爱的食品。夜晚具有代表性的小吃是新鲜的檀香橄榄。这一果品吃起来略带一点涩味,慢慢地则变成了令人愉快的轻微的甜味,具有清新提神的效果。人们相信橄榄可以帮助度过寒冷的夜晚,它是上海人最喜爱的食品之一。
另一种大众化的宵夜是粥,即用糯米和莲子做甜甜的稀饭。小贩备有蒸煮食物的火炉。他们的叫卖声打破了寒夜的宁静:“火腿粽子啊!白糖莲心粥啊!”老主顾已等了很久。当他们一听到这叫卖声,立即从二楼的窗户放下一只装着钱和碗的竹篮,在寒冷的夜晚跑到屋外可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1933年,小说家张恨水正住在上海,他的书斋是天津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亭子间。小说《啼笑因缘》于1932年至1933年在《新闻报》上分期连载,流行一时,因此张决定做一名作家。事实上,当时张正同时为十家出版社写小说。社会交际使得张白天十分繁忙,因此他习惯于夜晚在书斋写作。卖粽子的小贩的到来成了张吃夜宵的信号。张的妻子,在上床睡觉前,总不忘提醒老公:“倘有小贩喊卖火腿粽子,给买几只。”
卢大方,一位曾长期生活于上海的作家,回想起某天晚上从弄堂小贩那里买了一碗馄饨,从而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在上海那段放荡生活的“催化剂”。那个与其命运相关的夜晚,卢正和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弄堂里的一间房子内欢快地聚会,这是“旧上海”的典型的沙龙。大家玩得很开心,当参加者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到了午夜。
“我们饿了,听到了弄堂里‘笃笃’的声音,”卢写道,“那是卖馄饨的来了。女孩脱下她们的长筒丝袜,扎在一起,成为一根绳子,一头系着篮子,从窗口放下去。鸡蛋味的馄饨,一碗接着一碗,吊上了我们所在的三楼。大家一起享用着美味。”四十年后,陆在香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碗热腾腾好吃的馄饨导致了他生命中第一次的性体验,她是聚会中的一位女孩。
卢大方的逸事给上海弄堂里的本是司空见惯的晚间生意平添了一种风情。如卢所述,在经常而又定时交易的基础上,顾客与商贩之间已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每天,小贩们准时在弄堂里出现,已成了居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几乎所有卖馄饨的小贩其经营时间为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他们沿着确定的路线从一条弄堂走到另一条弄堂。这样,在某一特定的里弄他们差不多每天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当听到“噗噗噗”或“笃笃笃”的声音,因小贩使用不同类别的竹板而有所差别,老顾客准备好了盛器和钱钞在门口等着,或者从窗口吊下一只装着钱的器皿。
小贩收好钱,没几分钟便盛好了一碗热腾腾的馄饨。馄饨薄薄的皮–煮熟后皮变得透明了:里面的馅(猪肉或虾肉)呈粉红色,与绿色的葱花、黑褐色的香菇、金黄色的蛋皮、以及咸芥根相互映衬。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已成了无法抗拒的夜间美味。
**邻里关系和流言蜚语
根据居民的职业特别是大部分人家都有能力住上一房一户的情况看,正明里尽管不是十分富裕,也还可以算是一处小康的住宅区。在一些拥挤的住宅区里,居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彼此之间更加知根知底。绝大部分的里弄房子是联排式的,人们住在隔出来的房间内。在这种环境里,邻里之间的联系往往远超出于仅仅是讨论租金等问题。石库门住宅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比新式里弄密切得多。一般而言,房屋品质越高,居民之间的联系越少。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ShanghaiNeighborhood.jpg
上海里弄的夏夜闲聊。(资料图片)
拥挤的里弄有时是自成一个小小的社区,邻里之间没有多少秘密可言。就象有两位历史学家注意到的那样,在这种社区里,无论何时只要一户人家有客人上门,邻居们都会来问好。如果一家有了困难,大家也会伸出援助之手。邻里之间分享着彼此的悲痛和欢乐。甚至当一户人家包了馄饨或饺子,也会与他们的邻居分享。人们可以放心地上班工作,如果突然下雨,隔壁阿婆会帮忙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人们也不必担心偷盗之事的发生,邻居会帮着照看以解除后顾之忧。对此上海人可以说:“远亲不如近邻。”
对于习惯于住在比较有隐私环境中的人而言,这种邻里关系是恼人的,因为个人隐私常常会受到侵犯。但住惯了里弄的居民一旦离开,他又会怀念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热情。1949年后的上海,居民们往往不情愿迁出拥挤的弄堂,搬入由工作单位分配的较为宽敞的新公房。这其中有各种因素,但舍不得老邻居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位迁入了新居的里弄居民在为地方报纸所写的小文中抱怨,在他所居住的新公房“要和邻居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他以前居住的红豆巷里,邻居们常常在夏夜的小庭院中一起聊天乘凉。回想起过去,他不禁流露出了一种失落感。“尽管不少邻居的谈吐粗俗甚至无礼”,作者写道,“乘凉的时间却充满着坦诚、友好和幽默……一旦有人进入了小庭院,他会忘记酷暑的闷热。夏夜每个小庭院里充满着快乐和笑声。”
夏夜在弄堂中乘凉是上海的风俗,在身心得到松弛的同时也为邻里之间增进友情。晚饭时开始的三个小时──晚上6点到9点(在7、8月份太阳要到8点才下山)──上海人称之“乘风凉”。走出酷热窒闷的房间,带着小凳子、扇子、席子,有时还带着饮料(其中盛行一种和绿茶一起泡的菊花茶)、瓜果(西瓜是最流行的),大家坐在弄堂里一起聊天。这就是里弄中的“沙龙时光”。
聊天的话题不仅仅是流言蜚语,还可能包括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民国时期上海的政治性的上街示威和工人罢工和市民们的这种交往也许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如何这种交往在传播政治活动信息方面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
邻居们讲着故事,互相闲聊,谈论新闻或时事,也增长了知识。这往往是关系比较疏远的邻居互相交谈的唯一机会。作家茅盾曾回忆1927年是他写作生涯的开始,那年夏天他住在景云里,“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哭声笑声,吵成一片。”
据称鲁迅的杰作《门外文谈》就是1934年他住在上海里弄时夏夜闲聊的结果,因此起了这么个名字。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的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
这里提到的话题除了语言和文学外都是那一年夏天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东西。夏夜闲聊是里弄住宅区中具有代表性活动。另一位作者所描述的里弄生活显然要比鲁迅的弄堂要贫困些,但夏夜乘凉聊天的景象却几乎是完全相同:
太阳渐渐地斜西了。弄堂里吹入一阵阵地晚风,于是穷人可以享点小福,从三层搁,亭子间爬了出来,上身赤膊,下身一条短裤,芭蕉扇一把,坐在弄堂里,这时,后楼阿大,灶披间的好婆等,不约而同的来集在一处。于是阿大与阿三阿四,大谈特谈,上谈玉皇大帝,中谈陈济棠飞机失事,下谈昨天某家娘姨,与某家车夫,在某处开房间。
聊天的话题不仅仅是流言蜚语,还可能包括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民国时期上海的政治性的上街示威和工人罢工和市民们的这种交往也许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如何这种交往在传播政治活动信息方面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
居民们生活里弄中可能感到很安全,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可能被别人近距离地观察着。不仅仅是他们家来了哪些客人,晚饭餐桌上有什么食物,谁经常坐黄包车去买东西这类事情很容易被邻居所知道,甚至恋爱和通奸在邻里之间也很难长期保守秘密。
的确,有时这些“小市民”好象很喜欢打探邻里之间与性有关的事情,假如据一项学术研究显示的那样,上海的小市民是二十世纪早期(尤其是在二十年代)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主要阅读者,那么对于里弄居民而言,邻里之间的暧昧故事是他们所阅读的爱情小说的生动再现。一位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教师曾这样描述他是如何发现住在三楼的邻居的秘密的:
那模样确乎是一个入时的徐娘,她用一个小大姐服侍,其余没有人。我起初弄不明白她是甚么路道,说她是做生意的,却不出门的时候多,男人也没有来,只有一个黑苍的西装朋友,每隔两三天来一回,有时过夜,有时不过夜。那西装朋友象是个外路人,年纪也要四十光景了,这当然是那个人外室。有一回,我突然瞧见一个穿着袈裟僧鞋的和尚,进了门直上三楼去,我不禁大奇,想那女人暗底里还姘和尚吗?我有意等那和尚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到晚上,那和尚下楼了,我觌面对他一瞧,却恍然大悟起来,原来那和尚不是别人,就是那隔两三天来的西装朋友,不过每次来总戴着铜盆帽,瞧不出他的光头,由此,那女人的秘密,被我完全发现,她却是一个和尚的外室。
这段文字所使用的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语气:对他人的事情十分好奇,喜欢谈论他人的隐私。所发掘出的丑闻当然就充当弄堂闲聊谈的材料。
(选摘自《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作者卢汉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部《上海屋檐下》之第五章《在石库门后》)
http://www.ucpress.edu/books/pages/images/8279.jpg
《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英文版。(资料图片)
**作者简介:
卢汉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对华学术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多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及地方史研究上独树一帜。英文专着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4平装再版;2005年中文版)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2001年颁发的最佳著作奖,为唯一的华裔学者获此荣誉。该书被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及中国学研究最集中的学术评论称为“一本辉煌的著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