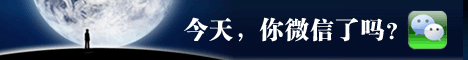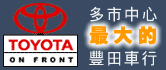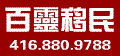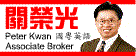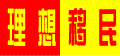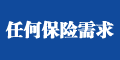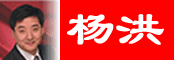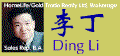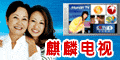李谷一与险成“亡国之音”的“乡恋”
编辑发布:jack | 2006-01-10 05:14:02
【星网专讯】时针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电视片《三峡传说》的编剧兼导演马靖华焦燥的踱来踱去:这难道是离别故乡的感情吗?太激烈了。我需要的是轻柔、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这个片子情愿不播出,我也决不迁就音乐!
作曲家张丕基,一副毫不妥协的神情:“我情愿不要音乐,也决不修改!”这是艺术问题的争吵,互不相让,火气冲天,复杂又单纯。如果没人来打破僵局,看样子得吵到大天亮。双方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李谷一的身上。
李谷一刚刚唱完这首歌,单就个人的情趣来说,她喜欢它,因为它容纳发丰富的声乐技巧,感情庄严,曲调高亢,为演唱者展开广阔的音域,适合她的胃口。但她凭直觉感到,这首歌很难在群众当中流行。因为除去她和某些专业演员,别人谁也唱不了。这不能不算做一点遗憾,导演人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她向作曲家说:“老张,再写一个吧。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保证给你唱好。”
编导和作曲家达成协议:由编导改写歌词,作曲家重新谱曲。
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赶写歌词。张丕基回家休息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这就是后来音乐界、评论界、观众中一场轩然大波的序幕。
有人说李谷一不唱《乡恋》是不是更好?或者,《乡恋》的第一稿不做修改,原样播出,是不是就能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躲过一违场灾祸?
――不见得。
在歌坛中,很少有人象她那样引起众多的争议,也很少有人象她那样曲折的艺术经历。她生长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十五岁考进湖南艺术学院学舞蹈。她在舞蹈系学习了两年,又不久被花鼓戏剧团招聘为演员,打下民族戏曲的功底。在中南地区会演时,由她临阵顶替《补锅》主要角色,一鸣惊人。
后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被撤销,李谷一下放到湖南湘西瑶族自治区,从一位小家碧玉成为以挣工分为生的农民。坚苦的生活环境,劳累的身体负荷,特别是长期餐不裹腹的时日,使她脱形而黝黑。这是她第一次经受生活的磨难,第一次感受人生的重压。
她还唱过民歌,唱过京剧,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学习西洋发声技技巧,十年寒窗,磨砺精深,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中央乐团的一位同志说,“她很会唱歌,很会表演,行腔咬字清楚,高音明亮结实,台风很可爱,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这各她从小学习戏曲、舞蹈有关系。她的声域宽,上得去,下得来,真声假声连接自然,流畅贯通,嗓子甜,有才华,音乐感很强。真是难得的人才……”
一个人倘若出了名,她所得到的赞扬和非议历来成正比。三年前,当她在首都舞台上初露头脚时并没有听到什么争议。她用浓郁的民歌情调演唱的《夫妻识字》,使老一辈闻到陕北高原的气息,唤起温暖的回忆。
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关心她,期待她,注视她的发展,有人希望她永远象可爱的延安小妞那样,有人盼望她冲破一切羁绊,也有人要求她走严肃音乐的传统之路。而她就是她,众口难调,每迈出一步,就失掉一部分听众,也赢得一部分听众。
当她唱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时,有人就发出煞车的信号――“到此为止”。当她唱到《小花》的插曲时,有人几乎不能容忍了。总之,她自觉又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艺术的、政治的、社会的旋涡,在演唱《乡恋》之前,围绕她的“倾向”问题酝酿着争论,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次日清早,作曲家张丕基还在酣沉的梦中,有人来敲门。睁眼一看,小女儿把一张纸放在床前。他匆匆浏览一遍,这是《乡恋》歌词的修改稿,写得很顺,便依在床头轻声地哼吟。他好象被施了魔法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松驰的、平易的、低回的旋律。八点钟,他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半小时后谱好《乡恋》的第二稿。
编剧惊异地说:“呵,这么快!”
作曲家说:“词顺就谱得快。”
两人相视而笑,昨夜的一场争论已经释然。这天大雪纷飞,他们当即派人前往中央乐团,把词谱送到李谷一的手里。
晚上,中央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当弦乐器和电吉它奏出过门的一刻,人们都屏住呼吸。这支歌将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谁也没有去预测。人们担心的是,李谷一接到词谱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毕竟太仓促了。她能够表达导演和作曲家所期待的要求吗?
她唱了。编剧和导演所规定的情景,作曲家所描绘的意境,唱得比想象中的更好: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这是一首面对着绮丽的三峡风光倾诉乡思离愁的抒情歌曲。姑且不去评价它在艺术上的高低、演唱方法的优劣,只说说录音室里的气氛。这是一首表达个人情绪的小品,如同悲欢离合构成了唐诗宋词中百读不厌的题材,最容易牵动人之常情,这首歌也出发埋藏在李谷一心中的感受。
她唱得真挚、凄婉、平白如话,如泣如诉,忧中怀有美好的憧憬。唱到动情之处,两颗晶莹的泪花夺眶而出。在场的导演、编辑、作曲家和技术人员傻傻地听着,如醉如痴,陶然忘机,在每个人的心中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乐曲结束时,导演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去关掉录音机的按钮。
“刚才你哭了!”作曲家对李谷一说。
她揩去了泪痕:“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
时值新年前夕,李谷一回到中央乐团后一片忙碌。联欢会、茶话会、演唱会……累得喘不过气来。《乡恋》一事,早忘在了脑后。在她的节目单上,《乡恋》只是即兴小品,唱过去就算了,并没有打算把它保留下来。如果不是一点火星引爆了一场争论,也许,命中注定它将是无声无息的。
1981年二月,《北京音乐报》率先对《乡恋》发起讨论。随后,读者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展开热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首歌是“灰暗、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有人认为是“明朗、健康的”,“优美动人的佳作”。有人认为它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和香港歌星的唱法”,有人认为“要允许模仿,学习的法则就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进而创新”。有人认为西方和港澳的流行音乐甚至包括轻音乐在内,“多数是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跳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密切相连的”,有人认为流行歌曲也有最为可贵的一点――“易记易唱,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还有人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打击乐器的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翻阅这些争论文章,令人惊异的是,对于同一首歌曲在听众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理解和反映,甚至对歌词含义的理解都相去甚远。
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你”指的是情人,因此断定这是消极的情歌,有人认为作者把家乡比做爱人,感情真挚而朴实。有人认为歌词中的“我”系指王昭君,让古代的王昭君唱今日的流行歌曲,与人物的身份不符;也有人认为“我”就是“我”,作者与演唱者的第一人称,跟王昭君毫无关系……
叽叽喳喳的、七嘴八舌的、甚至立论和命题都缺乏同一性的争执,展现了文艺界清新的气象――搞“一言堂”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时的李谷一在做什么?她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自从中央乐团部分地实行经济核算制度以后,浩繁的、沉重的演出任务加在她的身上,加在全体演员、职员的身上。而她所在的综合乐队更是负重如山。她已经累得两次声带出血了。
第一次是在1979年的一场内部演出之后。但在过去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休息和恢复。1980年她为十部电影片、电视片配置插曲,仅这一项就为乐团挣得好几千元的收入,她付出的代价是声带再一次受伤。
1981年三月,李谷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是答谢,也是答辩,说清了一些问题,另一些问题则说不清。她对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的处理而引起的不同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中国戏曲、民歌的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至此,围绕《乡恋》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限于艺术范畴。但在善良平和的争论声中,有人奏起尖锐的音符,对艺术家进行难堪的人身攻击,把李谷一比做“酒吧歌女”,说她“格调低下”,“对观众的庸俗趣味曲意逢迎”,这些同志是以维护民族风化、抵御西方侵蚀为己任的,但是他们针对一个女歌唱家使用的挖苦性语言,在西方的文艺评论中也不多见。
还有的同志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喇叭裤、港式头与音乐牵连在一起,甚至把艺术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混为一谈。进而有人疾呼:“亡国之音唱不得!”于是,艺术问题化为政治问题,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而社会主义江山在批评家的笔下被描绘得多么脆弱!
四月,李谷一正在南方巡回演出的途中,接到召开音乐座谈会的通知,从上海坐飞机赶回北京。会上,音乐界一位负责人点名提到《乡恋》,其它从事轻音乐创作的同志也人人自危。
李谷一的性格是泼辣的,她象诉说委屈的孩子,情绪激动:“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怎么学呢?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表达人民的爱憎,这就是我歌唱的灵魂!我今后倒要好好研究外来的音乐,我要买一台录音机,搞声乐的人能不研究吗?提起来都脸红……”
李谷一是坚强的。音乐座谈会散了,与《乡恋》有关的人员仍然背着卸不掉的包袱,李谷一匆匆离开北京,继续去南方演出。1981年上半年她总共演出二百多场次了,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她拿起扫帚清扫宿舍,忽然打了一个喷嚏,试了试嗓子,竟然沙哑失声,一个音也说不出来了。经过医生诊断,血管破裂,鲜血外溢,染红了整个声带。
这是她第三次出血。
养病期间她的心情是焦急的、烦闷的。她是为声乐艺术、为广大群众、也为她所在的乐团而效力泣血的。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她是团里的“摇钱树”,她的确尽力支持领导的工作。而她得到什么呢?她的手里保存着一封信,那是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几个月前写的,《乡恋》受到公开批判以后,经过别人交到她的手中。这封信对她的艺术倾向给予否定,指出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否则只有到适合的土壤去发展――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涉,象是最后通牒,也象逐客令!
这封信,与多次要她投入繁重演出的指令,出自同一位领导同志之手,未免不近情理。鞭笞一个演员的心灵,同时要求她发出优美动听的歌声,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辛酸和刑罚呵!
和这封信形成对照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的信。就《乡恋》一事,她收到上千封来信,其中九百九十几封都对她表示热切的同情和支持。
自从李谷一被点了名,一时成为人们口头流传的新闻人物。在当今生活中人们普遍奉行一条准则――从道义上同情弱者。人们在剧场里,在电视旁,关切地注视着她的举手投足、微末细节,神经变得极为敏感。人们关注的是她在压力面前是不是有所畏缩?
当中央乐团来到上海演出时,深夜两点就有人冒雨排队买票。一万八千人的体育馆,全场爆满。李谷一几次谢幕,几次返场。最后一个节目报出《乡恋》时,看台上掌声雷动。唱完后群众的情绪达到沸点,仍不放她走。结果,这个声乐演员不得不借鉴运动员的仪式,在体育馆绕场一周,向观众招手告别……
音乐界有的领导同志惊叹:《乡恋》不能再演下去了,因为这当中派生了其它因素!
李谷一在天津体育馆演出时,原订的节目单上没有《乡恋》。观众高喊:“《乡恋》!《乡恋》!”呼声潮起潮伏。乐队奏出了过门,李谷一开口演唱了,但是,观众的兴趣所在并不完全是欣赏艺术,全场和着音乐的节拍齐声鼓掌,直至曲终。他们的掌声是对李谷一的支持,也是对那些横加干涉艺术的做法的抗议!
生活在变迁,艺术在发展,观众的心理在转移。用音符去体现政策,用旋律去区分路线,用节奏去转变立场,有人试图这样做过,但收效甚微。那些为“四人帮”而高呼“就是好!就是好!“的乐章,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群众抛弃了。人们在饱受十年噪音的折磨之后,神经需要松弛。对流行歌曲和轻音乐所表现出的过于热衷,是对十年浩劫的惩罚。当然,对她的实践需要加以引导,广大听众的艺术修养有待进一步提高,而音乐界的领导也有改善的必要。文艺界也应吸取“沉船“事件的教训,人才的价值决不低于物质的价值。
(理由、邓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