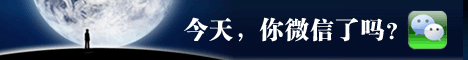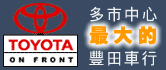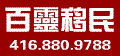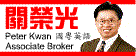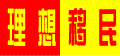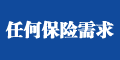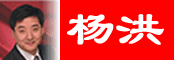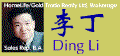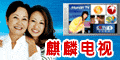跨国婚姻破裂后的夺子战争
编辑发布:jack | 2005-03-07 19:39:51
【星网专讯】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困局。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国际婚姻的一方,一个现实而苦涩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很多人要面对离异导致的子女归属之争。而跨国婚姻的特殊性决定了类似纠纷要遭遇法律、文化、习俗、观念的巨大差异。或许这是跨国婚姻必然要承受的风险。
**张宁娜日本夺子耗资300万
1986年10月26日,25岁张宁娜前往日本留学,这年的11月认识了40多岁的菅原喜仁,12月,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而此时的菅原已有妻室,有一儿一女。将之的即将出生终于使菅原做了决定,结束了和前妻的婚姻关系。
就在将之降生前的一个月,将之的日本籍爸爸菅原喜仁和中国籍妈妈张宁娜结束了同居十年的生活,登记结婚。“1996年,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菅原安排了夏威夷的旅行,并偷偷安排了一个浪漫的婚礼,为的是给我一个惊喜。”张宁娜的回忆里曾有甜蜜。
这是一个跨国的婚姻,在这个跨国婚姻之下还有跨国的经济贸易。“中日贸易公司”是菅原和张宁娜一手做起来的。
将之出生之时,正是公司最鼎盛的时期。日本的13家上市纺织公司被搬到中国,社长菅原被评为全日本100个优秀企业家之一。
将之三岁前,妈妈总是把他背在身上往来于谈判桌、工厂之间。在日本,妇女大多是呆在家里相夫教子的,但张宁娜要打理公司,中方的贸易全部靠她。毕业于经贸大学的她在经营方面显示出了才能,就算是在中国,张宁娜也要被归类于“女强人”。
这个家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感情的裂痕却开始出现了,直至局面闹到无法收拾。将之是跨国婚姻结下的果实。当这个婚姻出现问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将之留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
将之的爸爸要将之留在日本,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已经62岁,并且因为糖尿病恶化而双目失明。将之的妈妈在上海古北区的面向日本人的学校附近买了房,她希望将之在中国上学,她也好一边照顾将之一边做生意。
2003年8月10日,张宁娜从中国回到日本东京的家,发现丈夫、将之和保姆都不知去向,家里的门锁着,没有钥匙的她翻窗进入室内,看到了桌上丈夫给她留下的离婚决定。丈夫已经请好了律师。
2003年12月,菅原向东京裁判所申请将之监护权离婚前保全裁决,他认为张宁娜有将将之带回中国的危险,要求法庭将孩子离婚前的监护权判给他。张宁娜曾以全面停止中日贸易公司的中方业务为条件,与菅原谈判,希望以公司来换回孩子的监护权,可是菅原提出的条件让张宁娜不能接受。于是张宁娜停止了中方业务,公司宣布倒闭。
2004年4月,东京裁判所离婚调停不成立。离婚局面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双方都明白,除了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将之。“如果在将之和财产之间让我选择,我可以分文不取,只要将之!”张宁娜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
双方都请好了律师,亲情要一试法律的刀锋。将之的命运只能依靠法律裁决。
张宁娜说她不懂日本的法律,在她看来,年幼的孩子跟母亲生活是理所当然。她的理由有四,一是孩子的父亲双目失明,是一级残障;二是公司倒闭,丈夫的经济状况和她相差甚远;三是自己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没有问题,孩子的意愿也是跟母亲;四是日本10岁以下儿童83%左右都是给母亲的。
但是,一次次的法律交锋都让她大出意料。2005年2月18日,菅原喜仁和张宁娜的离婚案一审判决下达:准予离婚,孩子的亲权和监护权判给菅原喜仁。
如今,张宁娜已经回到上海,但她并不准备就此放弃,她还想赢回这场夺子之战。而现实情况清晰地显示,这个愿望的实现难度非常之大。
多位法律工作者一致认为,在此案中有日本籍身份的菅原喜仁多少占据了“主场优势”,而张宁娜的弱势在于在日身份不稳定,对日本离婚法律不熟悉,以及在法律背后的文化、观念、习俗等方面不占据优势。张宁娜在日本19年,竟一直拿着日本人配偶的3年定居签证,而孩子是日本公民,法庭会考虑作为日本人在本国居住生活,因此判给父亲的可能性就增强许多。与此同时,张宁娜为了公司的业务“一年有250天在中国”,成为她的致命伤。
日本报纸《中文导报》说:许多外国人称在日本的国际离婚是“BB”离婚,大多数日本人在离婚后会把一段失败的婚姻彻底斩断,不但自己不再见前妻或前夫的面,而且拒绝对方再看到孩子。
这份报纸说,日本的民法没有离婚后孩子会面的相关规定,虽然家庭裁判所承认会面一说,但却严格规定每月只有2个小时的会面时间。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日本没有免签条约,而日本也没有因“与孩子会面”而签发的签证,所以没有了监护权对中国母亲来说就等于永远失去了孩子。
张宁娜目前面临的就是永失孩子的危险。她说她并不知道在日本孩子的亲权是单方面的。她的律师始终没有告诉过她,当亲权判给一方时,就意味着另一方和孩子没有法律关系了,拥有亲权的一方可以将孩子过继给任何人,也可以不给妈妈。这是张宁娜不能接受的。一位母亲会因为一纸法律判决而被剥夺做妈妈的权利,这样的法律规定在世界其它国家并不多见。
东京家庭裁判所曾向张宁娜提出一个探视方案,规定张宁娜每两个月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张宁娜没有接受。目前对张宁娜不利的是,她有一个“人身保护庭”的案件在身,随时都有被取消探视权利的危险,而她的护照又将在今年3月15日到期。
“什么都可以割断,但亲情是割不断的。”张宁娜说,“儿子永远是我的,再严厉的法律也不能否定这一点。”残酷的现实已经呈现在眼前。自从拘留所一别,张宁娜再也没有见到儿子,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没有任何可以得到儿子消息的渠道。一年多来,张宁娜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每天晚上只有两个小时的睡眠,脑子都是儿子”。
在争夺儿子的大战中,家底殷实的张宁娜已经花去了300万人民币,这在一般的母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张宁娜正在准备继续上诉。“我可以不要命,但必须要将之。命都可以不要的人,谁还敢和我拼?”张宁娜像一只发怒的雌虎,怒目圆睁地说。
**熊晶的美国版“夺子”
熊晶的“夺子”故事延续了四年多,对她来说这是漫长的噩梦,而在美国她也因此成为新闻人物。
尽管纽约的律师团在最近作出决定,要到更高的司法机构为她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但显然,一切还遥遥无期。
这个被普遍同情的女人,几乎接近崩溃边缘。作为母亲,她已经两年没见过儿子一眼――连照片也没有一张。法官驳回了熊晶探视儿子的请求,前夫的妹妹带走了他,此后下落不明。记忆里关于儿子的最后印象,是两年前熊晶带着他“逃亡”到温哥华,在机场被捕时,儿子瞪大眼睛问妈妈我可不可以玩手推车。之后就被警察带走,与母亲失去哪怕只言片语的联系。
这足以让每个曾怀胎十月的母亲心碎。熊晶曾为此整日地哭,不受控制地在人前流泪,她焦虑紧张,精神脆弱。她的朋友对记者说,跟熊晶讲话要特别小心,再不能刺激她了。他们都很忧虑,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究竟还能支撑多久?
这场关于儿子争取权的噩梦,开始于四年前,“对手”是她的前夫,美国律师凯利。而故事的起初,却是以浪漫的形态开始的:一个婚姻遭受挫败的中国女人,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职业体面的律师。如闪电般,两人开始了一场跨文化、跨种族的婚恋。
然而这场浪漫只延续了两年,熊晶开始洞察到丈夫那些难以忍受的恶习:酗酒,嫖妓,暴力倾向。他们开始争吵,感情直转而下。第一次总爆发是在儿子毛毛出生的第十天,两人大打出手,一个被打出了鼻血,一个声称被花瓶“砸破了头”。
这次争吵以警察的扣押为结束。才十天大的毛毛由法官交给了熊晶的母亲邢美玲照看。不幸在几个月后正式上演:熊晶拒绝跟再次召妓的丈夫上床,被丈夫用枪指着头实施了“婚内强奸”,她报警,而其结果是,儿子被纽约儿童局带离这个“吵闹”甚至“危险”的家庭。
凯利因暴力被拘押,但他作证说,熊晶“行为失常”,“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失去理智”,法官因此判定,作为母亲的熊晶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临时监护权判给了凯利的妹妹,也是律师的希勒。
这一次错位导致了熊晶后来的若干痛苦。她自此不能自由地跟孩子见面,每周享受三小时被监视的与儿子相聚的时光。
然而,熊晶始终不能接受自己作为母亲被剥夺养育权利的事实,2001年6月的一天,她利用一次不被监视的探访,带着孩子逃回了中国。她没想到,这个目的简单的“爱的叛逃”,却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对美国警方来说,这不是一个母亲带走自己孩子那么简单的事,而是犯罪――一个没有法理监管权的女人,拐走了一个儿童。
这个美国快递公司的前程序员,因此“一举成名”。她成了各大主流英文媒体要闻版的“明星”――她和儿子的照片随处可见。就这样,熊晶不仅成为“国际通缉要犯”,而且在美国媒体和主流社会失分。没有人理解一个中国母亲的感情,她“背叛”的是整个美国司法体系。这是后来熊晶完全失去监护权的原因之一。
熊晶和毛毛隐居上海,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和安宁的日子。2002年底,凯利突然因癌症去世,熊晶考虑再三,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于是带着孩子返回美国。在加拿大转机时,她被捕了。一年后,她拿着在狱中给儿子织的蓝色毯子,走出纽约州威彻斯特郡监狱时,流着眼泪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我的儿子……我渴望把他长久抱在我的怀里。”
然而,直到今天,熊晶还没见过孩子一眼。姑姑希勒把毛毛藏起来了。她面对的不仅是像她前夫那样精通法律的律师世家,还有对她失去了信任的美国司法机构。
纽约华人界依旧给了熊晶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们组织专门机构,为熊晶筹款,做咨询,争取一些官员的同情。中国领事馆曾在2001年9月给美国国务院写信,抗议对熊晶的不公正对待。
**韦唯的“孩子保卫战”
与当初被广泛报道的跨国婚姻一样,知名歌星韦唯的离婚以及随后的“夺子”诉讼,也成为让人牵挂的新闻。
正在为母性而战的韦唯,会最终赢得对三个儿子的监护权吗?
“三个混血的儿子和韦唯一起生活在斯德哥尔摩,韦唯暂时取得了他们的监护权。”韦唯的经纪人陈玉生日前向记者证实。
“但目前还不是最后的监护权判定,韦唯要通过一个考察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韦唯要向有关方面证明她是有时间、精力陪伴和监护孩子的,只有评估合格后,韦唯才有可能得到监护权。”陈先生如此解释“暂时监护”的含义。
现在,韦唯正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只要孩子需要,韦唯可以放下一切奔到孩子身边。现在事业对于这位歌星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常常是工作进行到一半,孩子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一切都抛下―――陈先生如此描述韦唯的变化。
2004年4月,韦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首次承认已经离婚。在此之前她已经度过了一年的独身生活。韦唯与瑞典人史密斯结婚9年,生下三个儿子。韦唯多数时间生活在瑞典,但她的身份仍然是东方歌舞团演员,中国国籍。
“涉外婚姻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另外两人的年龄差异还是比较大,这种差异你能感觉得到。”陈玉生说。
当离婚证书拿到手,韦唯发现,瑞典法律和中国有很大差别,孩子的监护权往往悬而不决。一位知情人告诉她,有的案子甚至直到孩子长大仍判不下来。
离婚之后,韦唯一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因忙于国内的演出,韦唯把自己的母亲带到瑞典,并且在国内找了阿姨。外婆和阿姨除了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外,还给他们教中文。
“孩子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让我找到了奋斗的理由。我愿意放弃一切,拼了老命也得把孩子要回来。”韦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孩子的监护权,但史密斯也不舍得孩子。两人因此不得不对簿公堂。
瑞典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从经济能力和孩子利益最大化方面考虑,决定将孩子的抚养监管暂交韦唯负责。
作为父亲,史密斯担心韦唯将三个孩子带回中国,永远也不再带回去,就提前藏起了三个孩子的护照,“夺子”战在法庭外延续着。
现在韦唯已将三个孩子从马尔默转移到斯德哥尔摩。安排大儿子赛明顿读小学四年级,二儿子雷明顿读二年级,三儿子温森已上了学前班。
事实上,在史密斯的探视权方面,韦唯表现得很豁达――只要方便,对方随时可以探视孩子。但对史密斯来说,他要求孩子们去探望他,这样三个孩子就需要乘坐飞机或高速火车到马尔默去探望他们的父亲。
在孩子将来的居留权上,韦唯表示,他们将继续生活在瑞典,享受那里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孩子们也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她不会轻易改变孩子们的生活环境。
韦唯也试图让孩子们理解为什么父母会分开。她说三个孩子都能接受,在西方国家,孩子对此事都有很好的承受力和理解力,他们从小就很独立。
外表坚强的韦唯还是为离婚和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休息15天,工作15天,她必须陪孩子,为此推掉了不少活动,她需要找律师、心理医生,这时候工作就要停。”陈先生说,“有时候在国内演出时,因为想孩子她也会哭。”
在陈玉生眼中,韦唯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变得好起来,告别了不愉快的婚姻之后她反而更加自信了。而对于证明自己的母性,她显然更不缺信心。
**记者手记:法律条款之外是文化的冲突
采访张宁娜的时候,她的一句话让记者很震撼。她说,她从20多岁到日本,一直到现在40多岁了,从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日本人。包括她的丈夫。张宁娜说,很多时候婚姻是无奈,我们之间有鸿沟。
张宁娜的感觉应该是很多涉外婚姻男女主人公的感觉,这鸿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这也正是很多涉外婚姻失败的症结所在,离婚夺子只不过是这种深层次分裂的外在表现而已。
“中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涉外婚姻,更多的是为了功利的目的,因此总体婚姻质量不是很高。”多次接触涉外婚姻案的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点评说。
一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和上海市民政局的涉外婚姻调查显示,中国开放20年来,上海的涉外婚姻几乎覆盖了全世界,1998年达到4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但是上海女方和外国男方的结婚年龄却差了10.5岁,其中有13%的夫妻是两代人,整整差了20岁。离婚率之高似乎也不是意外之事。这份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结为夫妻的,离婚率为60%。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国妻子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0%,日本妻子和中国丈夫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5%。
而另一份来自日本的资料可以和上面的调查相互印证: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显示,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中,日本的国际婚姻离婚案件多达110871件,其中中日婚姻破裂约为3万件。从统计数字上看,日本的国际婚姻离婚案件中的夺子之争大多发生在白种人的父亲和日本母亲,或亚洲系外国人母亲与日本人父亲之间。孩子的国籍大多是日本籍。
孩子是婚姻的结晶,也是婚姻破裂后的“遗留问题”,孩子的血管里流的是两个人、两个民族的血液,这是谁也分不开的。
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许莉分析了这三个案例的复杂性。熊晶、韦唯的离婚夺子案,所在的国家分属于两大法律体系――欧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法律体系对婚姻、孩子的监护权的问题上的规定差异很大。即使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彼此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许莉强调,人身不是财产,很难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而不可协调的更多的是法律条款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甚至是习俗的差异。这是婚姻的根本冲突所在,也是法律的根本冲突所在。
当一个人嫁入异国他乡,就等于遵从了那个地方关于婚姻的理念习俗,当地的法律不会告诉你怎样过婚姻生活,但当地的习俗会教会你怎样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生活在哪一国的国土上就得受该国法律的规范,你很难拿自己的生活文化背景要求别人对你有所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国婚姻纠纷是一个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国际婚姻除了法律和对法律理解的冲撞之外,还有情感的、文化的、价值观的冲撞。这实在是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难题。
(选摘自南方网-南方周末,作者:南香红 孙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