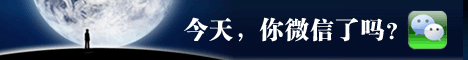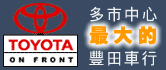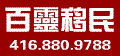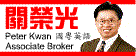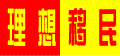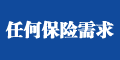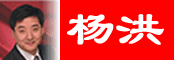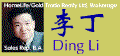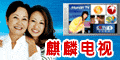麻将,华人为你而沈醉!
编辑发布:jack | 2006-01-25 17:00:13
【星网专讯】麻将,犹如历史的沉渣,追随著华人的足迹,飘洋过海,跨越重洋,至今仍强劲地吸引著天底下无数黄皮肤黑眼睛……
麻将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玩,具有深厚的草根性。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此物都甚得人们的青睐。无须讳言,搓麻将几乎成了华人最为迷恋的一种消遣,也是华人业馀生活中一种最普遍、占时最多的娱乐。
请听一个麻将迷的自述:“我真是叹服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除了火药、造纸、指南针外,还发明了这一百四十四块风靡了数百年的国玩――麻将。不可思议的是,一百四十四块花色不同的骨牌一经别具匠心的排列和组合,居然能变幻出无数惊心动魄的场景。这样,四个人一旦依各自摸定的东南西北入座,那小小的四方桌,便成了一个世界,一个风云变幻,魅力无穷,充满了壮烈奇诡,闪烁著刀光剑影的世界。”
“在这里,空城记、上屋抽梯、声东击西、欲擒故纵、走为上等计谋被运用得驾轻就熟。在这里,时钟仿佛成了著魔的风车,拼命加速,发疯般地旋转,十来个时辰给人的感觉只是转眼瞬息。在这里,人的大脑不歇地运筹著,脑细胞高度活跃,既要根据起手而得的十三个方块构划自己的蓝图,还必须因著随机而来的因素进行变化和调整,并且观察各人的神态、情绪乃至于出手时的坚定和迟疑,以探得各人阵中的虚实。既要有坐危城处险不惊的泰然气慨,又要有敏感善变的务实精神,其中的甘苦,也唯有入局者能够体验。由是,不知饥,不知累,唯有手中燃著的烟支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助人活跃思路,并且那红红的火点也象徵著克敌制胜的希望。”
“古人云:‘借酒消愁愁更愁’,酒确实不能解愁,而此物却能。无论你多么失意,无论你心中有多重的忧烦,一旦进入这个世界,顷刻之间都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此刻,一切的一切都会暂抛脑后,这就是这一百四十四块魔方的神奇之处。”
这一席对于麻将的叹语,委实道出了麻将的魅力,那就像是股不可抗拒的地心力,强劲地吸引著无数人,其中有做工的,有引车卖浆的,有写书作文的,有工程师甚至教授,总之,无论劳力者或是劳心者,无论穷人和富人,于闲暇中都钟情此玩,为之乐而不倦。
麻将素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赌具,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曾下功夫整治过,但可叹的是此物屡禁不绝,轰轰列列的禁赌到最后大都无功而返。当年蒋经国在赣州推行新政,年少气盛的他目睹社会上抽鸦片、打麻将的恶习盛行,痛惜不已,下定决心要根除之。其时商家夜晚歇市后往往紧闭店门,并将外层的铁栅挂上锁,在里面通宵达旦地进行麻将大战。蒋经国可谓用心别到,他采用微服查访的方法,在夜深人静之际,扮做卖夜宵的走贩,挑一付小吃担沿街叫卖,此时赌徒们鏊战了好几个时辰,正感到饥肠漉漉,闻听叫卖声更是食欲难抑,于是蠢蠢而动,卸锁开门,不想迎来的却是专员大人,于是一一被登记入册,次日一早到专员公署报到,情结严重者被罚跪烈士陵园,以起警示作用。其治赌虽严厉如此,但是敢于以身试法的赌徒仍有之。
四九年大陆政权易帜以后,新政府更是将麻将作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来加以扫荡,对搓麻将者的惩罚让人谈虎色变。笔者幼时有一次在夜半被呼啸的警车声惊醒,探窗而望,只见一辆警车就停在马路对面的住宅旁。次日一早,就听得邻居在私下议论,说对面那家人家昨晚因搓麻将被抓了好几人,再后来听说那东家被判刑送外地改造去了,从此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那位微驼著背、总是叼著一根雪茄的近邻。
那时为了一场麻将而毁却一生、害了全家的确实不乏其人,笔者一位小学里的同学,他的父亲虽偶尔涉足麻将,但并不是一个深陷麻将泥潭而不可药救的赌徒,一天他父亲因事去造访一位朋友,恰逢该朋友的俩位牌友前来邀战,于是碍于颜面,勉强入局。不想夜半被抓,判了三年教养,发配青海不毛之地。在那个年代,这虽然不算是很重的处罚,但是孰料名曰三年的教养却是没有尽头的无期徒刑,苦熬三年期满后并没有获释返家,而是更为绝望,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继续留在那片荒原上躬耕了二十馀年,最后郁郁而终。而他的家人则被冠之为坏分子家属,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抱著负罪感低头做人。所以,我的这位同学虽则聪颖过人,可是升学与他无缘,以致造成他孤独离群、忧郁寡欢的性情。每谈及此,他的悲怆不能自已,造成全家几十年的痛苦,其起因竟是一场麻将。
文革初期,在疯狂的红卫兵抄家运动中,收缴了大量的麻将,同时那些曾经在麻将大潮中戏过水的漏网之鱼又遭到残酷的清算。笔者的一个邻居,是个独居的七旬老人,早年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可能也曾迷恋过麻将,红卫兵在他的亭子间里搜出一付很精致的象牙麻将,这可不得了,红卫兵为之大做文章,他们在一个铅桶里放进一只沈沈的电熨斗,再将麻将牌倒入,然后将桶挂在老人的脖子上,桶上写著“赌鬼,社会渣滓!”他们还给老人剪了个阴阳头,让他久久地站在街口示众。谁会想到,一副麻将牌会引来如此的灭顶之灾!
文革结束后,人们从铁桶般的禁锢中舒过气来,各种娱乐活动也相继恢复,而对人心具有负面作用的麻将也开始还魂人间,并以雷霆万钧之势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也许物极必反是任何事物的定则,以铁腕治赌只能逞一时之威,而不可能达到持久的效果。
麻将在国内的复兴,起初像是一股悄然的潜流,缓缓地流淌著。那时都市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带著一种怀旧情绪,从箱底翻出逃过历次劫难、深藏了几十年的麻将牌,饭后聚在一起小战一两个时辰,这还不能称之为赌,因为他们是节制有度的,输赢只不过在块把钱之内,或则赢到的钱用于请客吃点心。与其说他们赌,还不如说他们在以这种方式重温他们往昔的生活,追忆那种消逝久远了的生活情调和生活环境。
偶而也有年青人在旁观看,于是麻将的薪火有可能接力下去,老年人在传授麻将技法的同时还讲述了他们自己人生途中和麻将有关的掌故和故事。对于生活枯索、急于求变的年青人来说,麻将既是一种新鲜的事物、一贴兴奋剂,又是一种和上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他们以好奇和近似虔诚的姿态从上一辈手中将几近绝迹的麻将技巧继承了下来。
然后,就像滚雪球一般,一批又一批的年青人相继卷入到麻将的娱乐之中,使麻将的队伍越来越大。而麻将队伍一旦注入新鲜血液,便充满了扩张的力度,它通过以一带十,以十传百的方式,以几何级数的惊人速度蔓延开来,简直一发而不可收了,很快就遍布到都市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项老少咸宜的“全民娱乐”。人们再也不讳谈麻将,麻将被公认为是一种富有智力性和趣味性的竞技游戏,而麻将牌的买卖也从街头巷尾的地下交易发展到唐而皇之地搁在商店的柜窗里公开销售。
于是整座城市都沈浸在麻将的热潮之中,你倘若夜间外出,看见亮著灯的窗口,探头一望,必是四人围坐无疑;如果你进入幽静的小巷深处,必定会听到哗哗的洗牌声不绝于耳;要是夏季,你还每每可以看到街口路灯下一桌桌露天麻将牌局,牌手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激情地运筹著。国玩在禁绝了几十年后又雨后春笋般地重返千户万家,成为都市的一大休闲方式,同时也构成了一幅幅妙趣横生的市井风俗图。
世上任何事物一旦进入失控的“无度”状态,就会像变得疯狂和可怕,犹如河道里以细胞裂变方式进行繁殖的藻类,一夜功夫可把河水变成腐绿。麻将运动在都市里无度地扩展著,很快它就成为一头蚕食人心的怪兽,成为一种极易传染的风病,成为一股畸形的社会时尚。
麻将的输赢从早先几毛钱、几块钱的小刺激发展到几十圆、几百圆的大出血,乃至一场麻将的赢亏可达数千圆之巨。麻将的操习时间也从原来的二、三个时辰发展到通宵达旦,乃至连续数个日日夜夜,欲罢而不能。其机率也从以前兴之所来、偶而为之的消遣发展成如餐饮一样,成为每日不可偏废的功课。
在麻将热的冲撞下,都市人像是发了疯、像是著了魔,各式各样的人生悲剧也纷纷在麻将桌上上演。因为和牌时高度亢奋,心肌梗塞猝然弃世者有之;由于用脑过度,脑血管不堪重负,中风瘫痪者有之;屡战屡输,借债垒垒,经济上拆东墙补西墙者有之;配偶苦劝无效,导致婚姻破裂者有之;为了赢钱鬼迷心巧,牌局上做小动作,造成朋友反目成仇者有之;输款巨额,心态失控,愤而殴斗伤人者有之……
对某些人来说,麻将已从消遣和娱乐衍变为一种生财聚钱的第二职业,甚至作为赖以为生的主业。
在麻将大潮的冲刷下,都市人真像是被勾去了魂魄,离开了麻将似乎就无所适从、寝食不思。每天同事间最热门、最激奋人心的话题就是“麻将经”,一早同事碰面,寒暄的第一句话多是:“昨夜手气怎样?”午间食堂饭桌上交头接耳、绘声绘色讲述的也大多是麻将桌上诸如力挽狂澜、反败为胜的精彩片断。各个科室、车间、班组时时都有昨夜麻将战况的“新闻发布会”,而且很快就会不径而走地传遍整个厂区。下班前一个小时内最重要的事是相互探底下约,筹组好工余的麻将战。每逢有去外省市出差的任务,也都要尽力凑成四人同行,以便在下榻的旅舍内可以随时成局鏖战,以消除旅途的劳顿和无聊。
麻将病的流行还滋生了更大的恶果,这就是麻将被用来作为权钱交易的工具。厂长、经理们美其名,将麻将称之为商业活动的桥梁,在商业交往中,每每于欢筵之后,在主、客双方酒酣耳热之际再附加一场麻将赛来压轴。于是贿赂的款项便可以通过麻将输赢的形式,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对方的口袋里,这能使其心安理得、免却了后顾之忧。
整个社会似乎都在为适应这股麻将热潮而进行改制,例如,有些高级的宾馆开设了特别的麻将套房,在起居室的边上辟有一间雅致的麻将室,一张带有抽屉的红木麻将桌和四把高背红木椅赫赫然地等候著下榻者的惠顾。等级差点的旅馆则推出出租麻将牌和出租简易活动麻将桌的服务,以使客来开颜、宾至如归,从而保持其营业额居高不下。一些个体商店的后室,都置有麻将座,供前来洽谈业务的用户娱乐,以联络感情。各个里弄社区也办起了老人活动室,名曰老人活动室,其实只要肯付费,壮年人同样可以入内进行麻将大战。
麻将的渗透力实在厉害,不仅国人被它迷得如痴如癫、废寝忘食,一些渡海而来、在中国工作的洋先生们竟然也被传染到了,甚至以生活态度严谨、工作作风一丝不苟著称的德国人也未能免俗。笔者的一个朋友在一家中德合资的汽车厂工作,他告诉笔者,一些德方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由于长年在中国工作,耳濡目染,加以受中方人员的言教身传,竟然学会了玩麻将,而且甚为投入,以此作为他们主要的业馀生活。同时,在麻将病毒的侵蚀下,他们的原则也丢失殆尽:休息天他们爱去旧家具店淘红木家具,请人修整后运回国,有时他们会带了些换下的旧红木料到厂里,纵容工人在上班时干私活,为他们制成精致的麻将盒,将打斗用的“玩具”装点得更加具有华贵气息。
近年,听说国内的麻将席开始出现更上一层楼的新局面,大量装璜高档、设施齐全的营业性“棋牌室”应运而生。许多人不再在家里开席,而是将麻将席转移到开设在社区里的棋牌室中,这样便免去了主人准备茶水和结束牌局后的清洁善后工作。棋牌室用的全是进口的自动洗牌桌,每桌费用为每小时20元,供应茶水,如果用膳的话,费用另加。政府部门有时也会装摸作样来棋牌室巡视,但只要在桌面上没有发现现金,就权作它为健康性的娱乐而不予阻止。
总之,国内都市里现今流行的麻将风,令一些由旧社会过来的麻将老手都自叹弗如,惊呼:看不懂!
六年前,笔者离开麻将娱乐如火如荼的都市上海,来美定居,意想不到的是,初到纽约不久即领路到了异国的麻将风光。其时笔者在唐人街人力中心学计算机,中午饭毕总爱到近侧的哥伦布公园休恬片刻,所见情景令我惊愕,公园简直就是一个华人的麻将俱乐部,麻将牌局一桌又一桌,比比皆是,虽然大多数是白发老人,但是其中也不乏壮年汉子,一个个都全神贯注、甚是投入,旁边还围著不少摒著气息的观战者,其盛况不亚于国内所见。
有一次突然听得有人叫喊:“警察来了!”牌桌上的操手们处变不惊,只见他们迅速地将自己的筹码抓起放入口袋,又敏捷地合手将麻将牌灌入一个包中,然后作鸟兽散。公园很快平静下来,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紊而不乱,和警察作这样的迷藏,他们一个个都像是受过训练一样。半向之后,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于是牌局又开始一一恢复,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们的同胞身居异国,在艰难的谋生之余依然如此执著于传统的国玩,并训练出如此一套对付警察的身手,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
在纽约,华人经营的地下麻将赌馆也为数不少,时而可见报载地下赌场所发生的斗殴乃至血案,警方对它的跟踪和突击取缔也屡有所闻,但总是难以禁绝。笔者有一次在唐人街懈逅一位上海的邻居,惊讶之下把他拉入一家咖啡店小坐,问他何以会来纽约,他告诉我他是通过商务签证单身来美闯荡的,目前在一家超市打工,问到他的生活状况以及是否想家。他笑著告诉我,他如今过的是集体生活,四个同乡合租一套两室的住房,白天他们各自去打工,晚饭大家轮流做,每人承担一个星期,开销平摊。饭后四人正好凑成一桌麻将,这样,沈浸在亢奋的拼拼杀杀中,最易想家的夜晚也就被轻易打发过去。不知道是因为人麻木了,还是因为生活充实了,总之,觉得日子过得飞快,思乡之情也自然淡却了好许。
和上述华人集聚地的麻将景观形成反照的是,在一些华人稀少的地区,麻将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绵绵乡愁。一次,笔者到新泽西州一个僻远的小镇造访一位朋友,他带著我在镇上游览了一圈,然后拐入一家华人开的小理发店闲聊。店主是一对来自台湾的中年夫妇,那先生说,在这镇上开这样一家理发店算是开对了,西人都乐意光顾,生意不错,日子也自然过的平静安稳而又小康殷实,只是他的太太耐不了这种寂寞,最不称心的就是这镇上没有麻将可搓,故而经常吵著要回台湾。他太太接著说,赚钱也不就是图个快乐,以前在台湾最大的乐趣就是饭后一场麻将,现在虽然手中有了钱,可是这种乐趣是再也没有了,镇上没几个华人,找谁去玩。又说她实在忍受不了告别麻将后的失落,所以已经对先生下了最后通牒,若入秋再不考虑归计,则只好分道扬镳,自己一个人回台湾去。她的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往昔那种麻将生活的追忆和留恋,她对乡土的眷恋之情似乎全倾注在对麻将的思念上了。
笔者每天上班要经过皇后区的一个食品超市,总看到一个华人老者将一袋袋拾来的易拉罐投入回收机里换钱,听他的说话口音,可断定他自己的同乡,于是不禁起了恻隐之心,想他何以会沦落到这个田地。有一天和他攀谈起来,问他何以不去找份工,收益再差的工也强似拾易拉罐呀!不想他笑哈哈地说,打工有什么好,受老板的气,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多不自由。又说他已到了退休年龄,还有何求,每天拾个六、七块钱的易拉罐,中午到附近的老人中心吃顿便宜的午饭,然后在那里玩几小时输赢不大的麻将,几块钱足够应付一个下午了,这样的生活如闲云野鹤,何其自在快乐!
他堆著一脸的诚恳和天真。看著他那付安天乐命、怡然无欲的神情,我怀疑起来,麻将难道真是诱人堕入黑暗深渊的恶魔吗?节制有度的卫生麻将不正在为无数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乐趣和生机,并抚慰著游子们的乡愁!看来,麻将的善和恶关键在于一个“度”,有度则有序,无度则为疯,而疯则是可怕的。我突然想起台湾一份曾经对台湾文坛起过重要作用的刊物《文学杂志》,它就是由台湾的几位大学教授和文学同人在麻将桌上的洗牌声中开始酝酿,并日复一日地在这洗牌声中逐渐完善了具体的实施构划。于是后来有人作了“谈笑而兴,麻将万岁;江河不废,文学千秋”的对联来纪念这份刊物。
麻将也确实是个能够使人陷入疯狂的尤物,笔者国内的一个同事,甚好麻将,但在麻将场上又总是失意。有一次笔者问他,既然麻将令他运交华盖,为什么还如此醉心此物,何不趁早割舍,可他的一番话令我为之哑然。他说:“麻将之所以难以禁绝,根源在于人生来就有一种不服输、想扳本,以及求刺激、爱冒险的赌博心理。与其说人生是一个拼搏的战场,不如说是一个交织著成功和失败的赌场,可不,人人都在赌,只是赌具和筹码不同而已,玩股票是大赌,买彩票是中赌,而搓麻将则是小赌。有人扔掉一个饭碗去谋求更好的,这同样是一种冒险,是一种赌博,相比之下玩玩麻将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是有毒的东西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所以有人会舍命吃河豚;有人明知吸毒会成废人,可还是要去染指;对麻将而言,输钱固然痛苦,可麻将的真正乐趣不在于结果,而在于那种跌宕起伏、激荡人心的格斗过程所带来的心理体验!”
(《彼岸》杂志,程应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