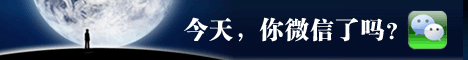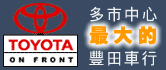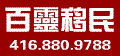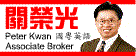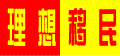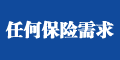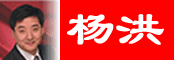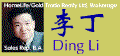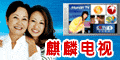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悼念香港一代宗师刘以鬯
发布者:北京四合院 | 2018-06-10 14:31:32 | 来源:多维
【星网专讯】
纪念刘以鬯:他影响了王家卫 是香港文坛一代宗师

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王家卫
一代宗师
从英军进驻中国殖民地的第一天起,陆地总面积不过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就站在了历史的最前线。两百年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十年动荡和1997年成为香港演变进程中的四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在战乱时期,作为敌对双方都默许保留的“自由港”,香港成为数万南人客居之所,他们参与到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业建设中,在铸就今日香港繁盛的同时,熔炼出现代香港的底色。但是,身处异乡,卷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洪流,又让他们对香港的“错位感”有更深刻的认识,其中,刘以鬯和王家卫是这一群体中不可忽略的名字,而他们二人之间,又有不少微妙的契合。
因为一个字,认识一个人。第一眼看到刘以鬯,头脑中有一个问题——鬯怎么读?原来,《刘以鬯和香港文学》一文介绍得很明白:“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
如果你喜欢王家卫,你一定会对刘以鬯的文字一见如故。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原籍浙江镇海,1918年生于上海,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受新感觉派的影响开始创作,1948年因战争原因奔赴香港,从此以作家、批评家和报人的身份逐浪文坛,是香港文坛的“一代宗师”。
而他的“弟子”王家卫大名鼎鼎,则不需赘述。他比刘以鬯小40岁,1958年出生于上海,5岁就随父母移居香港。在香港,王家卫大量阅读沪港文人作品,并受谭家明等前辈启发,决定拍出记录一代港人精神困境的电影,《阿飞正传》三部曲可谓代表作。
在大陆,刘以鬯名气并不高,文学圈外的人知之甚少,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他的《酒徒》《寺内》《对倒》等小说,都是干净利落的作品。他写小说不拘章法,充满实验性质,但也因此不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刘以鬯真正被一些圈外人知道,源于电影《花样年华》。
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编为电影,但绝对是最著名的一次。早在1946年,就有上海导演改编过他的小说《失去的爱情》,可惜年代久远,知者寥寥。但对于文艺青年来说,王家卫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电影在文艺圈子里传播甚广,于是,当文艺青年得知《花样年华》改写自《对倒》,他们就慕名闯入了刘以鬯的文学世界。
小说家陈子善说:“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这话不假,刘以鬯启发了王家卫的创作。《花样年华》《2046》受到了《对倒》《酒徒》的启发,甚至一些电影“金句”,原来也是刘以鬯赠予王家卫的,比如《花样年华》的这一句:“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又如《酒徒》那令人过目不忘的开头:“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王家卫虽没有直接照搬,但他镜头里一些情节,就是这种“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的感觉。落雨天里,女人靠在生锈的栏杆旁,“睁着眼睛做梦”。
酒徒对倒
有香港媒体报道过,因为看了《酒徒》,王家卫亲自去《香港文学》杂志社拜访刘以鬯,后者赠予他一本《对倒》,王家卫一口气读完,被《对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样年华》的故事。到2013年,95岁的刘以鬯回忆道:“他们拍戏时候,曾经叫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花样年华》杂糅了《酒徒》与《对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靠给报社写黄色小说谋生,这个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则神似《对倒》里的淳于白与亚杏。王家卫十分佩服刘以鬯,他在《花样年华》的片尾字幕里特地感谢了刘以鬯,自此以后,“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酒徒》和《对倒》是两部怎样的小说,能令王家卫心悦诚服?可以说,它们是刘以鬯的风格的代表作。其中,《酒徒》更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比王蒙的意识流书写早了二十年。在这部小说中,刘以鬯勾勒出一位堕落又自省的南下文人。他在《酒徒》中以自己为原型,讲述了大陆文人在香港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通过主人公在纯文学与商业化中的摇摆,以及人在理智与眩晕中的游移,探讨南下文人的精神困境。
《酒徒》有很深厚的现实依据。在五六十年代,当一批文人客居香港,他们首先要面对两个问题——物质贫穷与语言障碍。1956年,作家曹聚仁坦言:“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很穷;香港这个商业市场,随着战争到来而萎落的经济恐慌,谋生更不易:所谓‘文化’,更不值钱。”为了养家糊口,大批香港文人投身娱乐业、报业、影视行业,一边写黄色读物,一边捣鼓剧本、新闻评论。文人心气高,自降一格,内心难免挣扎,置身于资本世界的巨兽,个体的弱势昭然可见。刘以鬯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酒徒寥落,面临对倒。“亚杏走出旧楼,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这句话是小说《对倒》的开篇,《对倒》的故事很简单,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在旺角逛街的心理变化。所谓“对倒”,本是邮票学的专有名词,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据考证:有一次,伦敦吉本斯公司举行拍卖,刘以鬯写信去竞拍,拍得了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在用放大镜端详品相时,他产生了用对倒手法写小说的念头。在小说中,《对倒》指的是两个人在心里和地理上的擦肩而过。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不可挽回。
实际上,影响王家卫的作家有很多——普伊格、太窄治、韩子云、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村上春树乃至明代的笔记体小说家(《醉古堂剑扫》),都启发了王家卫的创作,但在精神上最契合他的,还是刘以鬯。他与王家卫,表面上讲男女情爱,深层里说的是香港地理、文化和精神上的错位。《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重庆森林》里的两个故事、《花样年华》与《2046》的时间隐喻、《一代宗师》的“天下南北”论,都是王家卫对这个大主题的阐释。比王家卫更早,刘以鬯在《酒徒》《对倒》中就探讨了香港在精神、文化和地理上的错位,他将这种错位感浓缩于主人公身上。除此之外,刘以鬯还写过一篇名为《一九九七》的短篇小说,对香港处于时代交接处的困惑与迷茫揭露很深。
海上花开
刘以鬯有他幸运的一面,因为家境殷实,从小沐浴于消费文化的“一线”,他不必忍受这屈尊的折磨,又能直观感受都市的新裂变,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良好的教养和启蒙令刘以鬯有很高的社会责任心,在前半生,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报人,他曾主编过《国民公报》《扫荡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鼓励一批新人的创作,如也斯、西西等小说家,都受过他的帮助。
后来,刘以鬯自己开始写小说,他自称“写稿匠”、“写稿机器”、“流行小说作家”,为了支撑自己办的文化团体,“煮字疗饥”,几十年下来,写了六七千万字,出版的书却不多。《文化中国》的一篇报道提及:“刘以鬯在出书时不惜大刀阔斧,把它们改写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简掉,更多的是被他称为“垃圾”而整个地丢掉。”无独有偶,刘以鬯的朋友东瑞先生回忆过:“《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刘以鬯、王家卫,这两位游走在上海与香港之间的“现代派”,文本间总是产生奇妙的互文,这绝非偶然。某种程度上,出生上海、移居香港的王家卫,自觉选择了最让他有共鸣的人作为导师。他们都对海派都市文学情有独钟,骨子里,上海才是连接他们的纽带。
中国的新感觉派乃至张扬着现代主义气息的都市文学崛起于上海并非偶然。在新旧剧变的时代里,地理位置优越的上海受资本扶持,幸运地成为早熟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搭电车的人搭电车,电影院墙边贴着新潮女郎的海报,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上海是少有的与伦敦、巴黎、纽约气质相近的城市,也只有这样的土壤,才能孕育出李鸥梵说的摩登文化。
刘以鬯本人正是站在上海新感觉派的肩膀上进步的,他的文学风格承袭自新感觉派,又对鲁迅的批判、自省精神有所继承。刘以鬯做的不是意识流化的鸳鸯蝴蝶小说,而是关怀内心、反映时局的华文现代主义文学。无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对他人的扶持,他都紧紧围绕这一目的。
不同于师尊高尔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主流中国作家,刘以鬯主动将乔伊斯、伍尔夫等现代派小说家的文学奉为圭臬。他曾在《酒徒》的序言中说:“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技法乃“自根至叶”,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只能触及现实的表面,“不但缺乏深度,抑且极不科学”。”刘以鬯希望“运用横截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里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来“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
阅读《酒徒》和《对倒》,我们能清楚感受到刘以鬯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容易叫人上瘾,读过几页,就刻在心里,在下雨天回想起。刘以鬯的小说故事可以浓缩在寻常的一天,运用大量的心理活动,排比、复沓、重复、矛盾、断片式的句子、潮湿混沌的氛围,他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以对人物刻画的深度见长。这些特点,亦见诸于王家卫的电影。后者如此执迷于手摇摄影,和那些被部分人批评故弄玄虚的句子,实则是为了营造这种意识流的氛围。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刘以鬯并不认为意识流是一种流派。他曾说:“意识流是小说写作的技巧,不是流派。它和“内心独白”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酒徒》)这本书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在技巧和方法上,算是个尝试。我写流行小说,是在“娱乐别人”,写《酒徒》,则是“娱乐自己”。”
值得留意的是,刘以鬯不是一位单纯的西化作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很感兴趣,在小说创作中,刘以鬯经常写出戏仿、解构中国古典名著之作。如:短篇小说《蜘蛛精》改写自《西游记》,作为禁欲符号的唐僧却在蜘蛛精面前坐怀不定,夹在色欲与道德之间倍感煎熬;短篇小说《崔莺莺与张君瑞》改写自《西厢记》,“崔莺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脑子里充满不可告人的念头。她想着牡丹怎样沾了露水而盛开”;短篇小说《蛇》里,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神话被彻底颠覆,许仙病态似的心理让人触目惊心。小说道:“那条蛇不再出现。对于他,那条蛇却是无处不在的……白素贞的体贴引起他的怀疑。他不相信世间会有全美的女人。”刘以鬯对经典的戏仿和解构,多少受施蛰存的启发,施蛰存曾写过一些解构《水浒传》《金瓶梅》的小说,对一批文人影响深远。从施蛰存到刘以鬯,这些解构性质的文本价值还需要时间检阅,但的确是大胆而有趣的尝试。
不仅如此,刘以鬯还对民国左翼文学保持关注。过去,一些文学评论片面地介绍刘以鬯,仅仅发掘出他都市风情的一面,却不细查刘以鬯的民族情结、社会意识,因此导致结论偏颇。事实上,刘以鬯不仅喜欢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文人的作品,也对萧军、萧红、端木肆良钦佩有加。在给学生介绍文学作品时,刘以鬯谈了不少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品,比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艾芜的《山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同时,他曾写过一篇《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的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谈论动荡的时局、飙升的物价对作家的巨大影响。
后半生客居香港,刘以鬯仍怀念上海。毕竟,他的童年和文学启蒙都在上海,“孤岛”不只有骚动,还有一派理想气,以及柯灵、施蛰存、穆时英这些文学“老师”。如果寄给他一本《繁花》,刘以鬯许是会一见如故,那是大陆作家金宇澄的作品,写透了世俗上海滩。
王家卫也在寻找上海。《阿飞正传》里,张国荣是香港人,她的养母却操着一口上海话,吴侬软语与粤语的对碰不是一种偶然。而在最近几年,恰恰是王家卫要到了小说《繁花》的翻拍权。
只是,思念应征着“失不复来”,那些积灰的岁月,在记忆里,也只能留在记忆里。2018年,刘以鬯先生100岁了,人到百年,世事洞明,文章生活,也已经豁然开朗。作为香港乃至中国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刘以鬯的小说虽不宏大,却必将留在文学史中。倘若将功名成就搁在一边,最令他感慨的,也许还是一个个故人的离开,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訏等南下作家,现在都一个个走了,白发老人独坐床边,看香港电车来来往往,一切止于沉默。
但外头仍然骚动,香港仍在剧变。迟暮之间,天要落雨。现在,作家刘以鬯准备回家了。
不想一去就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