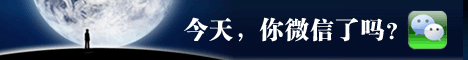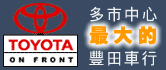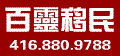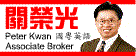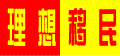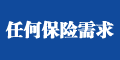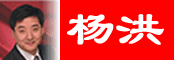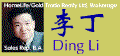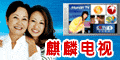旅加华裔作家张翎谈其书著《金山》与写作
发布者:会跳舞的面包圈 | 2011-11-28 10:12:25 |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星网专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法文近日出版。11月初,张翎借来法国西南部城市布里夫参加书展的机会,在巴黎凤凰书店,与法国读者见面。
小说《金山》以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一代华工远赴美洲“淘金”的史实为起点,纵跨一个半世纪,横越太平洋两岸的故土与异乡,描绘出在历史的起落沉浮中,几代华人背井离乡的苦辣辛酸。作者以小说的形式给予那些在异乡僻壤荒芜了的墓碑以生命,也以小说为载体,讲述了老一代华工鲜为人知的历史。
废弃的碉楼—未圆的梦
讲述老一代华工故事的想法最早萌生于1986年张翎刚刚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年的秋天。在与友人出游观赏秋色的途中,偶然在杂草丛中看到的几座字迹斑驳的墓碑,触动了她的灵感。几乎二十年以后,一个同样偶然的机会,广东开平一系列早已人去屋空的碉楼使她联想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市郊外那些孤零零的墓碑,因为这些像碉堡一样的住宅正是那些远赴美洲淘金的华工用他们的血汗钱为家中留守的妻子儿女修建的。
张翎:“我当时想,这些碉楼是关于什么的呢?碉楼是关于女人的故事。那是些被男人们留下来的女人。她们生活、居住在碉楼里,每时每刻都在指望着丈夫可以什么时候归来,或者丈夫不归来,至少有钱归来。所以,这是一群女人的梦。我就把这两个故事―男人的,和女人的,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了这本书的构架。碉楼是男人们在外边的一个美丽的梦想。无论多少辛苦,无论受到多少苦难,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有一天,居住在碉楼里的那些人能够同他们团聚,他们能有幸福的、富足的家庭生活。但是,这个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打破。所以,无论是碉楼里的人,还是碉楼外的人,他们人生的梦想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金山》的法文版书名正是《金山梦》。
华工的故事—人类迁移历史的缩影
小说《金山》讲述的是几代华人在与国他乡奋斗的故事。但张翎希望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华人的故事,也是所有从世界各地移民美洲,参加新大陆建设迁移者的故事。
张翎:“我同时也希望法语的读者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这是关于中国人的书,但又不完全是关于中国人的书。其实我要讲的是上个世纪人类的迁移的故事。在讲中国人移民做苦力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在同样的时间,爱尔兰人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美洲,在澳洲,在新西兰,正大批地移民,去兴建所谓的新大陆。意大利人也走向世界各地,他们帮助建起了多伦多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类的迁移,整体的人类生存状况,都是非常艰辛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生活在今天的人过着很富裕的物质生活,生活在相对平安,平等,自由的大环境里,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的祖先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今天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一位法国读者向我们介绍了她的读完《金山》后的感受:
读者:“这本书有两点对我有所触动。一个是这些碉楼中的人物。这些碉楼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它们承载着某种期待。它们应当在出现水灾、或强盗时,给予楼中之人某种安全感,但同时,这些碉楼又好像是魂灵出没的场所,让我们看到那些逝去的远赴加拿大劳作者的魂灵。这些人经历了非常艰辛的劳动,通常情况下,他们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只相处了很短的时间。
另一个触动我的内容是书中的女性人物。那些婆婆,那些没有名字、只有姓氏的传统女性。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她们来自某个家族。但是,慢慢地书中开始出现比较有个体存在的女性,尤其是那位在赌场、在茶馆挣钱的女性。我们并不知道她真正的职业。她在书中的名字是猫眼。后来,她和她自己的女儿关系很困难。女儿最终离家出走。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逐渐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这也是我觉得很值得一读的内容。”
张翎与写作
张翎1957年出生于杭州。1983年从复旦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后,曾从事翻译工作。1986年起,她定居加拿大。九十年代中期,她在从事听力康复师工作的同时,开始以中文写作。已经发表5本长篇小说,4本中短篇小说集。《金山》是她第一部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品。
张翎在读者见面会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法广:您谈到早在 1986年刚刚从北京抵达加拿大的时候就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如今已经有20多年了。回顾当年,您是否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这个故事会触动您,让您有了写作的冲动?
张翎:我想,我一直都是很有触动的。没有立刻就写的原因,是因为巨大的恐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我对自己是否能胜任这样一个巨大的考验心存疑虑和恐惧。这是为什么(写作)推了这么久的原因。
法广:那当时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您,让您有这么强烈的写作欲望呢?
张翎:我想始终是关于人的故事。任何理念都不能撼动我,但是,人的故事,那些细节,会非常深地感动我。如果我在教科书里读到关于华工的句子的话,它们不会感动我。但是,华工留下的一行字,一个墓碑,华工的妻子们留下的一件衣服,这是可以挑动我作为小说家的那种激动的材料。
法广:观察老一代移民生活,您化了很多心血,做了很多研究。您自己是新一代移民中的一员,也看到了新一代移民不断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方涌向西方国家。新一代移民与老一代移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么?
张翎: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需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都需要经历把自己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上连根拔起的疼痛。不同的地方是,老一代移民不太会有那种奢侈的欲望、有时间去了解这个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新一代移民,总体来说,国家现在强大多了,经济状况都很好,不需要为生计这样地奔忙,他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这个世界。
法广:书中的人物,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在西方国家都遭受到歧视。这种歧视和受歧视的感觉一直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种族歧视如今在西方国家也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在种族歧视的背后,往往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困难,面对眼前陌生的国家,面对自己的故乡。写作这些移民的故事之后,您对身份认同问题是否有新的认识?
张翎:我不太探讨文化身份认同话题。我的小说里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类命题。我更多地是想写人和人的故事。
如果有种族歧视存在的话,我觉得它的根源是一种无知和恐惧。。人对他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心怀恐惧的。现代人和当年的人不同的是 ,现在的人们在面临无知的时候会说:我不知道你,但是我想了解你。但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彼此无知的人群就会把自己锁在固定的碉堡里,不会出来主动了解别人。我觉得社会已经在发展、进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存的话,唯一的方法是和平相处。
法广 :那写作这本书,您的收获是什么呢
张翎:我的收获是第一次知道作为小说家是如此艰难,尽管过去也发表了很多作品。写作的过程虽然困难不是很大,但是围绕写作的那些工作的艰难程度是扒我一层皮的。在写作之前,我料想会扒我一层皮。但写完之后我才知道,它不是扒我一层皮,而是扒我两层皮。
法广:写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张翎: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和必需。对别人来说,写作也许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写作不是选择:不写,就会死;写呢,我是受苦受难。在受苦受难和死亡之间,我没有选择,只能受苦受难。
法广:您在加拿大学习过,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您观察身边世界,对社会事务,对人性的认识是否也有影响呢?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张翎:最大的影响是,我在(听力康复)诊所工作的这17 年,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些是战争的难民,有些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涌到加拿大来的。在我的诊所里,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经历了战争、饥荒等各种各样的灾难带给这些人的创伤。所以,我对痛苦这个话题有更深的认识。
法广:《金山》并不是您的第一部著作。您自己认为最满意、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您自己感觉最身心投入,也在写作之后有一种身心得到释放的作品又是哪一部?
张翎:我想,哪一部也没有让我感觉身心释放,好像每一部都把我更深地卷进一种深深的哀伤里。但总体上讲,《金山》应该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书,但是不是我最重要的作品,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创作生命还很长。再看将来罢。
法广:到目前为止,您一直以中文写作,主要的读者群是中国大陆的读者,作品也都在中国大陆发表。您在构思、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考虑:我的读者在中国大陆,有些东西可以写,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写?
张翎:从来没这么想过。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但是,我觉得对自己要诚实。好像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我自己。我要对自己诚实,我把自己当成是诸多读者中的一个。如果我用真诚感动了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也能用同样的真诚感动我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