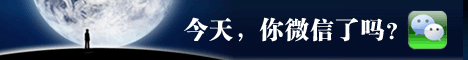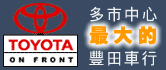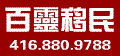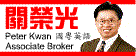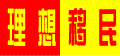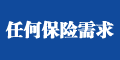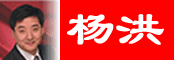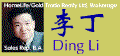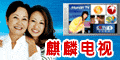美国何伟 火在中国
发布者:北京四合院 | 2014-09-21 07:27:50 | 来源:共识网
【星网专讯】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探讨过移民群体生态,而何伟的妻子张彤禾也在2013年出过一本畅销书《打工女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三人有共通之处,即都属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者,都对中国底层民众向上发展的路径有过实地采访和切身体验。
2014年9月,美国记者、作家何伟(本名Peter Hessler)逗留中国数日,日均接受一家以上大大小小的媒体采访,俨然成为文化类媒体的宠儿。何伟此次中国之行是受大陆数家媒体联合邀请,除宣传新书《奇石》之外,还与不少媒体人、作家、读者交流对谈,开讲非虚构写作、与学者对谈中国话题……他引起的这股媒体追逐热也印证了自己在读者粉丝群体中的认可度和号召力。何伟为什么在中国媒体和读者圈中这么火?他又是怎么火起来的?
很多人最开始知道何伟这个名字缘于一本书——《江城》,之后,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陆续出版,虽然晚于台湾译本的推出,但在大陆年轻读者中仍然赢得不少拥趸,“何伟热”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栗子:三部曲中的《甲骨文》一书先有了台湾繁体中文版,但在大陆却至今未推出简体中文版,热心的读者粉丝当然看不过去了,于是自发翻译出此版并流传于网络间,用他们的话说,一切都源于看过《江城》之后被何伟的文字所打动。
能够用心观察并用富于细节性的文字描述出中国人都不曾关注到的中国现实,这是何伟让不少读者心生敬佩之处,如果追问一句:何伟走近中国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并写出如此纪实性的文字,最初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在促使他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难道仅仅是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志向使然?对此,何伟在自己的书中有过“接地气”的回答——“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指涪陵),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善于捕捉细节的“外国人视角”
何伟最早是于1996年来到中国,那时是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涪陵支教,1998年来北京后成为外媒驻北京记者,一直在中国待到2007年才离开。在涪陵近两年的生活催生出《江城》这本书,而寻访河南安阳古遗址、南京明朝石碑和中山陵园的经历则被写入《甲骨文》的开篇。与今天受媒体热捧相比,90年代刚来北京时的何伟却还不是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而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当时,在北京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所有的东西都在电脑化,这样一份早已过时的工作算是让何伟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显得枯燥、无前途,但小小的记者站却让何伟感到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
有国内媒体曾评价,“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观察视角上的独特加上逐渐流利的中文能力,让他更有机会来直接表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观感,那么,他的“外国人视角”都观察到哪些我们习焉不察的东西呢?
当何伟从北京搭乘火车去往河南安阳时,他写道:“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然而接下来,单是外国人关于中国河南的文章或著述,何伟就引用了四个出处:1981年同样搭乘火车前往安阳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1930年曾住在此地的外国人理查德·道森,1880年造访此地的美国人詹姆斯·哈利森·维克逊,以及19世纪时写出一本中国游记的西方人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很明显,他的文字透出的这股怀旧文艺范儿在一般中国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中,有谁会去花时间耐心地考察自己居住地的久远历史乃至祖父辈的人生经历?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再比如关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递烟这件事,他就有过一段记述——
2001年,何伟驾车来到浙江丽水市,在那里他的采访对象有一位土地被政府低价征收的农民。何伟不知如何开始对话,他递上一根烟,对方羞涩地拒绝。
“真的真的,不要客气。”何伟用蹩脚的中文说。
农民接受了。他们聊了十分钟。
“再抽一根吧,真的真的。”何伟递上第二根烟,他们又聊了十分钟。
当第三根烟递到眼前的时候,农民告诉何伟,他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
何伟回顾,正是在这家工厂采访时,他发现递烟是一种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刚开始别人给我烟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并立刻拒绝,后来我发现这似乎不太礼貌。于是我也试着学他们的方式递烟给别人,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改变了,产生了一种更舒服的相处模式。”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者
何伟说,他喜欢中国的小城市甚于大城市,与接触专家学者相比,他也更愿意跟中国的普通百姓聊天。他解释,“名人们通常很忙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于记者的问题,所以从他们那儿无法得到很多内容。但是如果去采访一个从未接触过记者的人,内容会有趣的多而且通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普通人那里的信息更接近真实。”
在何伟笔下,描写过的小人物中包括一批从中国内陆地区流向北上广及东部沿海城市的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这让笔者想起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中探讨过的移民群体生态,而何伟的妻子张彤禾也曾在2013年出过一本关注沿海城市打工者的畅销书《打工女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三人有共通之处,即都属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者,都对中国底层民众向上发展的路径有过实地采访和切身体验。比如,在参观南京时,他特意寻访了明朝永乐皇帝为朱元璋雕刻的巨型石碑,他写道: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处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人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记录中国社会及其变迁,这本不在何伟的计划之中,他从小的志向是成为一个作家,他读过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但大都不太喜欢,他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在他居住在涪陵的90年代,“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中国)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但在何伟看来,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只是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事实上,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正与全国上下一样经历着变化,在涪陵生活了18个月之后,何伟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与美国大学写作老师的通信让他有了写书的打算,之后开始做大量的调研和翔实的笔记。他周游四方,在江边跑步,在涪陵的茶馆喝茶看书,游三峡大坝,站在江边看白鹤梁水文石刻,跟四川人喝白酒较劲,远走甘肃、新疆体验域外风情……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习惯在口袋里装着笔和笔记本,以便随时收集和记录各种东西,包括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
何伟的几本书中涉及了中国的许多核心议题,包括文革、国企改革、三峡工程,但他很少选择著名的政治事件或文化人物来解读,而是选择叙述普通人在大事件中的命运沉浮,这种既亲历中国人生活同时又保持适当距离的观察者身份,无疑让他的文字变得独特,比如,他在《江城》中写道:“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对这段文字,有人赞其观察敏锐,有人则批他惯于猎奇,但笔者看来,何伟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或许能很好地予以解释——“当时写书的时候是为了给美国人看的,我想中国人并不会喜欢。但出版之后中国读者的反应令我很惊讶。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正在变化,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