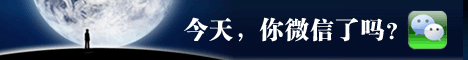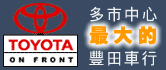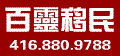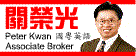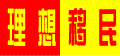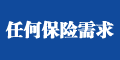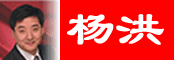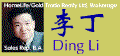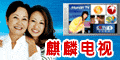陈又津/土人、唐人或华人?印尼华人的称呼与认同流变
发布者:炸酱面 | 2021-02-06 11:22:11 | 来源:独立评论在天下
 “印尼华人究竟是印尼人,还是华人?” 图/美联社
“印尼华人究竟是印尼人,还是华人?” 图/美联社
印尼华人究竟是印尼人,还是华人?阿雪阿姨在吉隆坡看到花布和传统乐器会说,“这是我们的,但是被马来西亚说是他们的。”无论真相是什么,她为印尼不平的怒意是真的。尽管她在新加坡买房,但也不想定居,就算新加坡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便利的交通,还是比不上雅加达。她只是为了将来情势动荡,有个地方可去。这也是我母亲来台湾的原因。
一个人的多重表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研究东南亚,《想像的共同体》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最后也在印尼爪哇逝世。他父亲是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的爱尔兰裔,保母是越南人,为了躲避战争,安德森在美国求学,但他在美国学校有英国口音,到了英国学校也有爱尔兰腔。
我们今日使用的中文/华语同样有腔调的差异。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被台湾人称赞“国语讲得很好”,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母语(或是地方话以外的第二语言),只是我们常常对这种腔调充耳不闻。
印尼在30多年的华校华报禁令影响下,30岁以下的年轻华人几乎不会说华语,但华人的概念依然存在。他们读天主教学校、去华人开设的商店购物,交朋友和嫁娶的对象也多是华人。只是这些华人,就算去了所谓“华人的地方”,例如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常常也不被视为自己人。华人或许不只是媒体所说的“富人”,最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人。
印尼有17,500多座岛屿,确切数字始终不明,因为这国家有许多活火山,不断有岛屿因火山喷发而消失,也有火山岛每年从海平面缓慢升起。这些岛上有数百个种族,例如“温和”的爪哇族,或是“粗鲁暴躁”的曼都拉族。虽然这样说有某些共通性,但依然只是个标签。认真要找的话,应该也能找到温和的曼都拉族人。
印尼人称呼洋人为“Bule”(发音Boo-Lay),意思是白人,像是中文语境的“洋鬼子”,有点歧视的意味。《A Geek in Indonesia》的作者就是个典型的美国白人,久了以后,他也入境随俗称自己是Bule。但他也认为印尼人要有政治正确的概念比较好,不然因纽特人永远都是爱斯基摩人,达悟族依然是雅美族。
至于中文用“黑人”指称非裔美籍人士,但直译回英文就是“Black people”,虽然比Negro的歧视意味低一点,但在美国,没人敢在公共场合明目张胆说出“Black people”。但到底怎么称呼黑人在美国也是莫衷一是,有Dark-Skinned、Dark-hued、Brown等说法,讲的都是皮肤,换汤不换药。另一种称呼是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之类,问题是,黑人到美国都几百年了,怎么会是非洲人?
我问过来自英国、美国、南非等地的老师,究竟该如何使用“Black”?老师说,虽然这是不对的字,但我们私底下若都清楚对方的意思,还是会使用Black这个字。其中一个老师是美籍非裔韩国混血儿,外表看起来不是典型的黑人,她说这个字一直让她很困扰。
例如她去看病时,医生问她父母来自哪里,她答美国和韩国,结果医生在黑人的地方打勾。她宁可被说是“那个穿黄衣服的女生”、“站在角落的人”、“手上拿着蛋糕”——有那么多方式可以形容一个人,但偏偏只有她的皮肤被看见。
 印尼华人或许不只是媒体所说的“富人”,最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人。 图/路透社
印尼华人或许不只是媒体所说的“富人”,最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人。 图/路透社
人,可以这样被轻易分类吗?
至于中国,长久以来在印尼语是Tiongkok,由闽南语和潮州话而来。后来日本统治期间改为Cina,有负面的意义,苏哈托执政后也沿用下来,近年才改回Tiongkok。印尼民众也许以为Cina是个惯称,但至少官方电视台都开始修正了。倒是华裔以客语、闽南语称呼印尼当地人为“番人”一点也没改变。至于母语就是印尼语的这群年轻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其他种族的人了。
但从日本时代的日本人视角的著作,例如鹿野忠雄的《山、云与蕃人》来看,那时汉人是“土人”、原住民是“蕃人”,对殖民者来说都是异类。进一步细看,所谓的华人也不都是同一种人。如孔复礼(Philip Kuhn)在《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中研究,印尼和马来亚华人也有语言和宗族的边界,分为福建人、福清人、兴化人、客家人等。台湾课本提过“漳泉械斗”,就算种族相同,但语言、文化就足以造成隔阂。先来者占了商业地盘,后到者就只能找寻其他空间。
我的母亲家族这边用客家话自称“唐人”,唐山过台湾,虽然唐朝的势力从来没到过台湾和印尼。孔复礼写道,越南也有“明乡人”的说法,意思是“仍然思念明朝的人”:“1679年,粤藉和桂藉兵士大约3,000人,为逃脱清兵追杀,乘坐50艘战船进入了越南。”这些人被当做政治难民,定居于荒芜地区,甚至建立了武装自治领地。这些移民成了阮氏王朝对抗高棉扩张的屏障。
“客家人为了开矿,抵达了婆罗洲。垦荒对客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先前已经有人到邦加淘金。这些移民不全是非法之徒,也有怀抱梦想的生意人。”
“广东人大量向外移民基本是在19世纪成形的,他们一直在手工业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他们是灵巧的修理工、能干的小五金商人和小业主,同时他们还是小客栈、小餐馆的成功经营者。此外,潮州人以擅长种植农作物而著称。客家人曾经长期在边缘地区求生,其早期以出色的采矿者闻名于世,但后来不少人则转型经商,活跃于诸多城市的商贸领域。”
尽管后来明清时期有了海禁,但诡异的是,海禁并不禁止人民出海,返乡养老的人才会被敲诈。因为出洋的人举债做工,根本一穷二白。衣锦还乡的人才有油水可揩。1749年,富商陈怡老事业有成,甚至为荷兰政府担任“甲必丹”,管理调解华人事务。但清帝国规定人民出国不得超过3年,否则取消中国国籍,陈怡老又为外国政府工作,于是被逮捕、审判,流放到西北边疆。此一事件后,清帝国才放宽了3年限制,华侨得以无限期侨居异地。
19世纪时,世界各地逐渐废除奴隶制,但那之后,不代表人们自由了,只是由另一批苦力(Coolie)顶替。被欺骗、胁迫的工人上船了,运到遥远的地方。秘鲁的纪录是没有食物、没有通风,航程长达好几个月,苦力死亡率因此高达22至41%,死亡原因包括坏血病、痢疾、脱水,以及自杀。有时苦力的处境甚至比奴隶还惨,奴隶至少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但契约劳工就算期满了也不见得能脱身,小工头会聚赌或推销鸦片,让工人满身债务。为了利益,就算是彼此来自同种族,说着同样语言,一样会压榨彼此。
这些罗汉脚(移工)当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才有了“宗亲会”。宗亲会对于菁英阶级是象征性的地位标志,但对于普通华人而言,是在不幸亡故又无法葬在家乡时,能办个像样的葬礼。
 中爪哇省三宝珑傍河而建造的建筑,约1925年。 图/Tropenmuseum, par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中爪哇省三宝珑傍河而建造的建筑,约1925年。 图/Tropenmuseum, par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虽然不同却又相像的我们
随着时间过去,不同时代的“新二代”,在东南亚也有不同的称呼。
“在爪哇,此类异族通婚的后裔在马来文中叫作‘伯拉纳干’(Peranakan),意为‘土生’;在麻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此类群体称为‘峇峇’(Baba);而在菲律宾,则被叫作‘麦士蒂索’(Mestizo)。”
在爪哇,土生华人(Peranakan)是当地出生的移民后裔,新客华人(Totok)则是出生于国外的新移民。但我猜从其他族群眼中,看起来都是移民,有着同样的血缘。这样的愿望成为清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海外华人的寄托,希望遥远的祖国能保护自己,但也永远得不到居住地政府的信任。1911年的革命对于这些华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剪去满清王朝强迫的辫子,一方面恢复了汉族身分,也方便融入当地。
然而1854年,印尼法律取消土生华人的优势,降到印尼本地人的低点。而20世纪初的中国,承认所有的华人都是中国人,直到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1960年时,印尼政府要求华侨做出选择。19世纪下叶,澳洲政府曾担心若开放中国移民,中国文明会取代英国文明。
当我们提到台湾,可能不是一种血缘或种族。我记得几年前,一团新加坡高中生来台湾参加营队,在我的文学课上,那个新加坡高中生用掺杂福建话的华语说:“我知道芦洲,那边有很好吃的切仔面。”切仔面这三个字,说得十分道地。也有菲律宾母亲的女儿,长大到了兰屿之后,发现那边的原住民与菲律宾老家的语言相近,于是有了“新二代”的认同,希望去了解更多东南亚事务。
了解周围岛屿的身世之后,才会发现海洋不是边界,而是连结的纽带。不是谁去巩固了疆界,而是每个人都建立了连结。
(※ 作者:陈又津。曾任职广告文案、编剧、出版社编辑、记者。关注移民及城市议题。出版有《少女忽必烈》、《准台北人》、《跨界通讯》、《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我妈的宝就是我》。本文授权转载自“独立评论@天下”。)
 “了解周围岛屿的身世之后,才会发现海洋不是边界,而是连结的纽带。” 图/路透社
“了解周围岛屿的身世之后,才会发现海洋不是边界,而是连结的纽带。” 图/路透社